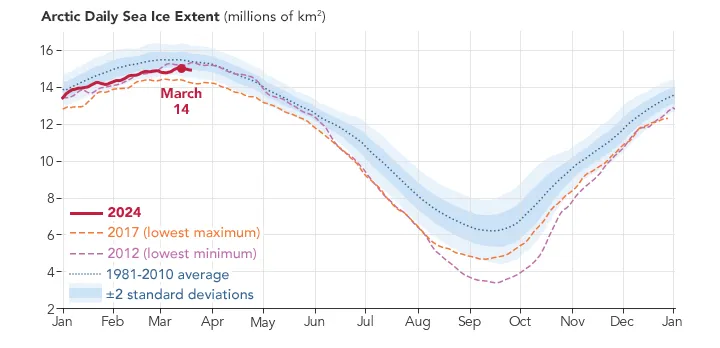有数十年亚马逊雨林研究经验的保育人士对COVID-19(新冠肺炎)的反思
亚马逊雨林东北边缘、巴西的马拉尼昂(Maranhão)地区,一棵孤零零的硬木树,在整片的森林砍伐中逃过一劫。 PHOTOGRAPH BY CHARLIE HAMILTON JAMES, NAT GEO IMAGE COLLECTION
作者托马斯. 洛夫乔伊(Thomas Lovejoy),1989年摄于巴西的亚马逊雨林。 PHOTOGRAPH BY ANTONIO RIBEIRO, GAMMA-RAPHO/GETTY IMAGES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THOMAS E. LOVEJOY 编译:钟慧元):一位拥有数十年亚马逊雨林研究经验、也是重要保育人士与生物多样性学者对COVID-19的反思。
就像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我也因为COVID-19(新冠肺炎)而避居。 这并非我人生遭逢的第一个全球大流行:我经历过还没有疫苗时的小儿麻痹大流行,那时候的父母会口无遮拦地在孩子面前大声讨论这种可怕的疾病,认为孩子听不懂。 那一辈的大人,有很多都经历过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 而这些年来,我们也都曾紧张地追着新闻,关注从非洲、亚洲和中东人类族群中冒出来的埃博拉、SARS和MERS。
除了小儿麻痹这种唯一的人传人传染病以外,这些致病媒介大都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只跟动物有关。 这些病毒会外溢到人类身上,是因为大自然的某些方面被扰乱了,这其中是有教训的。
如果人类继续大规模破坏自然,就不该被不断冒出来的新兴疾病吓到——其中某些新兴疾病也可能具备全球大流行的潜力。
黄热病的案例
有一个可能已经没那么多人知道的经典案例是黄热病(yellow fever)。 许多美洲国家、包过我以生物学家与保育学家身分度过整个职涯的巴西,都曾经碰上这种疾病肆虐。 黄热病是很久以前在非洲森林中演化出来的,到了17世纪,运奴船把这种疾病带到了美洲。 跟在发源地一样,黄热病会在人口密集的聚落循环,并藉由一种已经适应了和人类共存的蚊子(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运奴船可能也把蚊子从非洲一起带来。
在20世纪初期,大举扫除蚊子潜在的繁殖地,在预防方面达到绝佳效果。 从1937年开始,这种病就能靠有史以来最棒的疫苗轻松预防,只要一剂就能一辈子免疫。 巴西最后一次发生黄热病的城市流行是在1942年。
但这种疾病并没有就此消失。 因为就和非洲的状况一样,这种病已在南美洲的森林里站稳脚步,建立了一种通常称之为「丛林黄热病」(jungle yellow fever)的独立循环。 那里的病毒在树冠层中漫游,杀死吼猴(howler monkey)和其他种类的猴子;最近还侵袭了濒危的金狮狨(golden lion tamarin)的最后一个族群,地点就在里约热内卢的外围。
即使巴西城市已开始施打黄热病疫苗,每隔一阵子,总是会有人带着丛林黄热病从森林走出来。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懂人类到底是怎么感染到这种疾病,因为丛林黄热病的自然循环是发生在举头30米得高处。
身为研究生的我在伊万德罗. 查加斯研究所(Instituto Evandro Chagas)与解决了这个谜的人共用一间办公室,那就是迷人的哥伦比亚学者乔治. 波谢尔(Jorge Boshell)。 在他职涯早期在哥伦比亚雨林里看伐木工人砍树的时候,曾看到他们突然被小小的蓝色蚊子包围:那是一种趋血蚊(Haemagogus),是丛林黄热病的已知传播者。 这些蚊子通常只生活在树冠层、叮的是猴子。 因为人类砍倒了它们的家,才让它们有了叮咬人类的机会。
波谢尔目睹的景象,正是破坏自然会威胁人类健康的范例──而我们现在对自然的破坏更胜以往。 过去几年间,巴西已经出现了超过750个丛林黄热病死亡病例,是194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波疫情;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城市循环,政府也再一次展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
问题不是只有黄热病而已:亚马逊的森林砍伐也为疟疾(malaria)和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等疾病的宿主和传染媒介造就了繁殖场域。 而问题还不仅是局限在巴西或任何其他单一地方。 随着COVID-19全球大流行所强烈展现的,现代交通系统能迅速地将某些人类或动植物病原体与害虫带往全世界。 在我写稿的这个时候,一艘停泊在巴尔的摩港口的中国运煤船被(及时)发现上面有亚洲型舞毒蛾(Asian gypsy moth)的卵块,而这种蛾是至少500种植物的害虫。
轻贱自然是危险的
对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来说,COVID-19全球大流行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的近缘物种,也能在蝙蝠体内繁衍,而蝙蝠却大致免疫,不易受这种病毒的影响而生病。 中国武汉的野味市场,可能是这次病毒从动物外溢到人类身上的发生之处,而最早从野生蝙蝠跳到动物身上、而动物又被人类取得并吃掉,很可能也是发生在那里。 像这样的市场是动物虐待的梦魇,拥挤的状况和卫生条件都糟糕得要命──正是催生新病毒威胁最理想的罪恶渊薮。
中国在2月下旬发出了封锁令,禁止野生动物的买卖和食用,但这是否会成为永久禁令则不清楚。 每一起新的COVID-19死亡病例,都再度强调了关闭中国、南亚和非洲野生动物市场的重要性──同时也应确保民众能有丛林肉之外的其他选择──这应该列为国际公卫议题的第一要务。 同样应该受到控制(能消灭的话会更理想)的是野生动物走私,也要遏止栖地、尤其是热带森林的破坏。
大自然滋养我们。 是我们源起之处。 这次全球大流行给人类的教训,就是不要恐惧自然,而该是修复自然、拥抱自然,并了解如何与自然共存,并从中获益。
整个生物多样性基本上就是庞大的解药图书馆,已经接受过天择、演化、还有各种生物学挑战的测试。 举例来说,像是蝙蝠特异的生物特性──它们竟然对冠状病毒免疫──或许能嘉惠人类所需治疗的研究。 人类对存放自我成就的图书馆极为尊崇,绝对有理由抱持着相同的敬意,对待大自然的活图书馆,并悉心照顾。
像我这样的生物学家最讨厌人家问的问题之一,就是某人随便指着某种生物就问说:这东西有什么用? 那就像是从书架上拿一本书下来──连读都没读──就问说,这本书有什么用?
那么,病毒有什么用? 医学史上有位传奇人物,曾经在科学界尚未发现病毒存在的时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18世纪末,英国医师爱德华. 詹纳(Edward Jenner)注意到,罹患了名为「牛痘」(cowpox)的轻微疾病的挤牛奶女工,似乎不会再感染另一种严重很多的疾病──天花(smallpox)。 虽然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这两种疾病,但他推论,牛痘必定能令人对天花免疫。 身为一个有想法的人,他做了实验,证明牛痘的受害者不会感染天花。 看不见的牛痘致病原,其拉丁名称是Vaccinia(源自拉丁文的「牛」),最后催生了vaccination一词──也就是疫苗,是现代医疗的基础之一。
因为疫苗而得以享有更长、更健康、也更有生产力的人生的人不可胜数──为数当然有几十亿。 人类的生产力也相对加强了。 我们急着尽快做出COVID-19的疫苗,也因为登革热的疫苗似乎已经唾手可得而兴奋不已。 但是,有任何人曾经停下来,肯定、甚至感谢大自然和牛痘病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