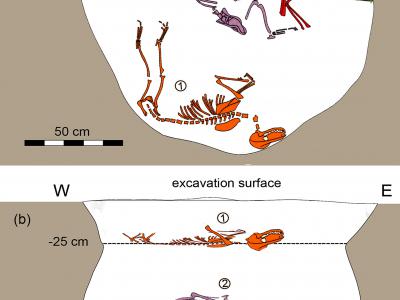元明时期西夏佛教文化的流传
核心提示
未有正史流传的西夏一朝,似曾给人以太多的神秘。然而,出土文献的发现使得这一情况得以逐步改变。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参照,使得人们不但对西夏一代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而且对西夏文化在后世的流传及其影响也有更多感触。
1227年,西夏被蒙古军所灭,但将近两百年的精神文化却难于瞬间消逝。党项西夏遗民在后世的活动以及西夏文化流传,曾一度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几年,这一现象再次受到学术界关注,尤其是西夏佛教文化在元明时期的流传随着材料的突破,给学术界带来了许多耳目一新的观点。
一
对于最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长达百年的老命题——元刊《西夏文大藏经》(通称《河西藏》),最近我们又获得了一些更为清晰的认识。存世的《河西藏》实物资料中,有明确标识的材料并不多见。笔者于2009年对这些实物资料作了系统梳理,这些材料多从莫高窟北区以及宁夏灵武出土,另有一件为山西太原崇善寺旧藏。依据这些实物资料不难归纳出《河西藏》的文献形制,进而也不难对那些没有明确标识的各种《河西藏》残卷作出判定。
目前所出《河西藏》多是杭州大万寿寺刻本。此版《河西藏》是在元初一行国师印制的《河西藏》基础上重新刊刻的。刊刻工作由鲜卑杜靖及知觉和尚慧中主持,于大德六年(1302)夏雕刻而成,十年之内先后5次印刷,共印190部。其中第二次印刷由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印,他并非此前学术界所言的大万寿寺本的雕印主持人。此版《河西藏》的刊印与《普宁藏》、《碛砂藏》等汉文南系大藏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1年,孙伯君亦就《河西藏》解决了许多关键性问题。她注意到大万寿寺本《河西藏》较西夏时期所译多出了四十一卷,这当是加入了元初一行国师新译的西夏文佛经。非但一行国师在入元后继续翻译西夏文佛经,在大德六年之后,仕元的西夏裔僧人如智圆、乌密二使等也在继续着西夏文佛经的翻译工作。孙伯君还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于正史或其他传世文献中勘同出了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涉及《河西藏》的几个关键性人物,如《元史》中立传的杨朵儿只、《普宁藏》本《正行集》卷尾跋语中提到的速古儿赤等。在这些人物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对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的考察。作者首先认可了王静如的观点,即管主八不是一个人名,而是藏文bka’-’gyur-pa的音译,其为藏传佛教对通经藏大师的尊称,与汉语“三藏法师”相当。进而指出,在元刊《普宁藏》、《碛砂藏》题记中,管主八似乎专指“主缘刊大藏经僧录广福大师”,并用大量材料证实了此管主八实际上是史籍中经常提到的白云宗僧录沈明仁。这的确是《河西藏》相关研究的重大突破,同时也将《河西藏》的流通和白云宗建立了密切联系。
二
事实上,元代西夏佛教文化的流传离不开白云宗的努力。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一部《正行集》,此前学术界多有误解,将其译成《德行集》,与曹道乐所编的同名著作《德行集》混同,视为儒家作品。2009年,孙伯君指出这部文献应该是白云宗祖师清觉《正行集》的西夏文译本,乃为佛教文献。白云宗于宋代元祐八年(1093)由清觉所创,其以《华严经》为立宗旨归,主张儒释道三教圆通,自创始以来,屡遭禁绝,至元代得以复兴。在西夏遗民胆巴上师、杨琏真加等释教上层官员的护持下,白云宗被允许在民间募资刊印《普宁藏》,清觉被尊为白云祖师或白云释子,其所著《初学记》和《正行集》也因此入藏于《普宁藏》中。
孙伯君认为,《正行集》可能就是在白云宗复兴以后的元代被翻译成西夏文字的。她还进一步梳理了黑水城文献中与白云宗有关的其他几部西夏文文献,它们是署名寂照国师的《求生净土法要门》、卷首附白云释子图画的《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以及活字本《三代属明言文集》。如果这些文献果真是在元代白云宗兴盛之时翻译成西夏文文献的,那么关于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的断代将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此外先前关于西夏时期活字印刷的一些观点也将面临挑战。
三
此前我们知道《河西藏》在元初由一行国师刊译,也知道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多部文献与其有关,但详情所知甚少,如今我们对一行国师又有了更多清晰的认识。在1996年出版的《洛阳市志·白马寺龙门石窟志》中有一篇铭文——《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塔铭》,崔红芬、李灿几乎同时注意到了这一材料可能与西夏文献中的一行慧觉有密切联系。铭文详细地记载了西夏遗僧一行慧觉国师的生平。结合这一铭文及相关文献,不难重构一行慧觉国师的生平及创作。一行慧觉俗姓杨,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其父曾是西夏高官,一行慧觉在西夏亡国后于贺兰山云岩谷慈恩寺出家,既修藏密,又习显教,主张显密圆融。后入洛阳白马寺拜龙川行育和尚为师,学习《华严经》,并随行育参编《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获赐“宗密圆融大师”之号。后应永昌王之邀赴凉州传法。行育逝后,推荐文才为释源宗主。1302年,文才去世,慧觉奉诏为第三任释源宗主管理白马寺,皇庆二年(1313)圆寂。一行慧觉流传下来的作品有《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四十二卷以及西夏文《涤罪礼忏要门》。一行慧觉刊译《河西藏》是在至元七年(1270),当在入洛阳白马寺拜行育和尚为师之前,以上西夏文作品可能也是他入洛阳之前的创作。
四
明代,西夏佛教文化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流传,先前我们熟知的材料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河北保定出土的明代西夏文经幢、北京云居寺收藏的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等。近来,学术界又注意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本泥金字写本《大乘经咒》,为明成祖永乐年间所作。一般认为,此书是集其时汉地民间流传经咒以及元代藏传梵本所传译的咒语而成。然而胡进杉先生指出,其卷二的《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实际上就是出土材料中所见的西夏时期鲜卑宝源翻译的汉文佛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不过其在陀罗尼的音译用字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大致可以理解为陀罗尼在流传过程中随着诵持者方音的不同而发生的改变,因为翻译者鲜卑宝源当时使用的是河西方音。这一大悲心陀罗尼也有未作变化而以咒文单独成篇且继续流传的情况。例如《永乐北藏》将其收入并命名为《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同时它还出现在永乐大钟的铸文之中。也正是从明代时起,各种《汉文大藏经》亦将其录入,易名为《番大悲神咒》。非但西夏《大悲心陀罗尼》在明代继续流传,笔者以为《大乘经咒》卷二的全部内容可能都与西夏旧著有所关联。
未有正史流传的西夏一朝,似曾给人以太多的神秘。然而,出土文献的发现使得这一情况得以逐步改变。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参照,使得人们不但对西夏一代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而且对西夏文化在后世的流传及其影响也有更多感触。最近的这些研究表明,也许在传世的佛教文献领域,结合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特别是在元明时期的佛教研究材料中,可能会发现更多西夏佛教文化的影子。
中国社会科学报 段玉泉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