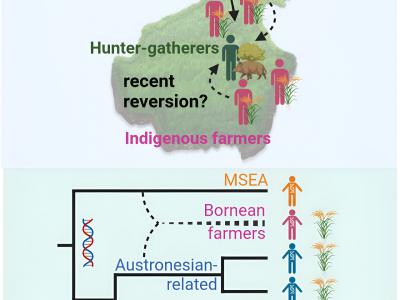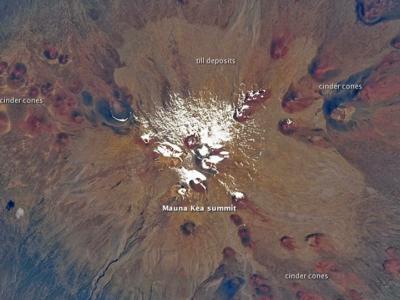伊斯兰国阴影下的伊拉克库尔德人
库尔德族年轻人有些穿着传统服装,有些着西服,参加苏莱曼尼亚大学毕业典礼。这个世代比前几个世代享受到更多自由。「我们可以用功读书,但战争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一名学生说。「或许我们的努力都会白费。」Photograph by Yuri Kozyrev
学生在阿尔巴特难民营上课时踊跃举手发言。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政府已收容超过100万人,他们都是从伊拉克与叙利亚逃避伊斯兰国战火的无辜百姓。 Photograph by Yuri Kozyrev
小女孩看着一名母亲(中)和她的女儿(左)及媳妇同时掩着脸入镜。这些女性都是库尔德族群内为数更少的亚兹迪人。图中的女儿和她的小姑说,她们被迫嫁给伊斯兰国战士,后来才逃到库德斯坦一处难民营。女儿为了逃走,还从二楼窗户一跃而下。 「我根本不相信自己能活下来,」她说。 Photograph by Yuri Kozyrev
在基尔库克南方,名为自由斗士的库尔德族部队在前线后方打排球。伊斯兰国战士(据信其中也包括前伊拉克陆军军官)自2014年开始在伊拉克境内攻城掠地,自由斗士是少数能阻挡他们的武装势力之一。 Photograph by Yuri Kozyrev
(神秘的的地球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尼尔.谢伊 Neil Shea 摄影:尤里.科济列夫 Yuri Kozyrev):摩苏尔被伊斯兰国(ISIS)攻陷的那一天,伯丹.夏巴尔哲里决定自己愿意一死。
这位24岁的大学生面带笑容离开父母在苏莱曼尼亚(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家,去买了香烟,再打了几通电话。他和许多朋友都在放暑假,所以毫不费力就召集到一群志同道合、愿意上战场的年轻人,他们满腔热情,但毫无经验。就在吞云吐雾及互传简讯之际,他们一起拟定了一套计画。有问题也很快达到共识。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楚、正当。他们都愿意为祖国牺牲――不是为了伊拉克,而是为了库尔德斯坦。他们誓死保护家人免受残忍的敌人荼毒,正如他们的父执辈曾对抗萨达姆.海珊的军队一样。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让他们证明自己的战场、一个往前冲的方向。
在伊斯兰国部队攻入伊拉克之前,夏巴尔哲里一直很躁动不安,有一搭没一搭地念着工程学位。他熬夜熬太晚,念书永远不够认真。总是对着方程式和统计数据打哈欠。音乐是他的最爱,乌德琴则是他的乐器。这是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琴颈细长,琴腹又深又圆。
除了公开演奏,夏巴尔哲里也加入了音乐家的俱乐部,梦想着灌唱片。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音乐产业即使在景气好时规模也很小,因此夏巴尔哲里担任老师的父亲很早就鼓励儿子转往比较务实的方向,像是造桥工程之类。夏巴尔哲里觉得进退两难。伊拉克的经济在崩坏,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希望。换成其他年轻人可能就会低头认命,说「是安拉所愿」。但夏巴尔哲里非常入世,反对各种宗教狂热者。直到2014年6月那一周为止,神的意旨对他来说,还没有忘记做作业来得重要。
接着,自称真神安拉军队的战士出现了,他们扬着黑色的旗帜四处烧杀,突然之间,夏巴尔哲里的生命有了目的。他在战争中找到一种他过去只有在音乐中看到的清明。每个选择都成了音符:只要好好地串连在一起,就可谱出他自己生命的乐曲。他没有武器,所以他会卖掉心爱的乌德琴去买一把AK-47步枪。他没有受过训练,所以他会加入一群受过战争洗礼的男人行列。他没有女朋友,所以没人会阻止他。他的父母如果知情,也会想办法阻止――可能会和他吵,会老泪纵横、会求他不要去――但有些事情男人就是必须去做,通常也就是那些他不会告诉母亲的事。
大多数库尔德族年轻人没料到又会有一场战争,起码不是这场由伊斯兰国发起的战争。不过几年前,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还非常繁荣。美国在2003年推翻了库尔德族最痛恨的敌人海珊,让库尔德族有机会掌控他们所居住、面积相当于瑞士的多山地区。虽然他们还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但基本上已形成了自己国家的雏型。这个地区很快就因为投资、开发的涌入,以及对石油开采的乐观预期(库尔德斯坦坐拥庞大原油蕴藏)而改头换面。摩天大楼在号称「库尔德斯坦的巴黎」的苏莱曼尼亚市拔地而起,库尔德自治区的首都霍勒市则罗列着购物中心、豪华轿车经销商以及义式冰淇淋店。大学相继成立。类似全民健保的制度也上路了。行销者甚至想出这样的口号吸引观光客和企业:「库尔德斯坦,另一个伊拉克。」当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地区正在水深火热之际,为数约500万的库尔德族人却进入许多人称之为黄金十年的繁荣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没有恐惧、充满了可能性――伯丹.夏巴尔哲里长大成人了。
「似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他跟我说。
「至少有一阵子是这样。你目睹这些事情发生。你看到大家的生活在改变。我当时还小,但已经看得懂。我父母、所有的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和夏巴尔哲里是去年年初在苏莱曼尼亚市的一家咖啡馆认识的,当时他已回到当地上课。他个子不高、长得很帅,经常留着一撮稀疏的山羊胡。
夏巴尔哲里有点跛地走到我的桌旁。数月前他在战场冲锋陷阵时被子弹打到――子弹穿过他的小腿――咖啡馆里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年轻人起身向他打招呼。小姐们则看着他窃窃私语。库尔德文化中很少有比这更伟大的荣誉象征了。
「奇怪的是,我再也不用排队了,」夏巴尔哲里说。然后这位退役军人脸红了,赶忙改变话题。他在参加补考,因为身体复原期间错过了一些课程。不过考试成绩挺糟糕的。
「我不太能专心在课业上。」他说话时用拇指摩挲着一串传统的念珠,不过他强调这些珠子没有任何神圣目的。 「工程学……真的很无聊。」
夏巴尔哲里和大多数伊拉克库尔德族人一样――不到30岁,普遍对未来怀抱希望,但那个希望正快速地消逝当中。对他和许多同辈来说,世界正在缩小、变得扁平。伊斯兰国虽然危险,但这些武装分子只是外在威胁。
对内,库尔德族的各个政党曾在1990年代打过激烈的内战,现在又为了权力和金钱议题争论不休。他们与阿拉伯人掌控的巴格达向来关系不稳固,现在状况更糟。为了石油收入的争议,伊拉克首都的阿拉伯领袖暂时扣住了应该分配给库尔德斯坦的联邦预算。黄金十年的欢欣鼓舞情绪正逐渐消散。
如果伊斯兰国可能毁掉一切,或伊拉克这个国家――充满腐败、无能而摇摇欲坠――可能会崩毁,那夏巴尔哲里实在看不出来上那些枯燥的课程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还不如都死光光算了,」他说,「这样也比继续过这种生活好。」那是一种很库尔德族式的表达方式。咖啡馆里大部分男性都会同意,说不定也有很多女性会赞同。她们都穿着紧身牛仔裤、浓妆艳抹。当你年纪轻轻、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如何能忍受失去自由?夏巴尔哲里决定要尽快回到前线。
库尔德族拥有独特的文化和语言,但除了历史上少数几段短暂的自治期,他们总是生活在更强大文化的阴影和控制之下――包括波斯、阿拉伯、鄂图曼及土耳其。现在居住在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及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族人据信有2500万人(不过确切的族群数量仍无从得知),他们常被形容为全世界最大、但却没有国家的族群。这或许是真的,但言下之意是指库尔德族是团结一致的整体。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库尔德族人说的是不同的方言,支持的政党都是一些规模很小、派系很多的地方政党。就算有机会,库尔德人也可能不会尝试联合不同地区的族人、共同成立一个更大的库尔德族国家。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最有机会独立建国。他们已有自己的国会、总统和输油管,更有一支名为peshmerga(自由斗士)的武装部队。继续归属于伊拉克似乎是必要之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的要求。海珊被推翻后的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库尔德族政府就暗示要脱离伊拉克独立, 而这总会激怒其强大的邻国土耳其和伊朗,以及南部的伊拉克阿拉伯人。不过库尔德领袖总在最后关头却步,让许多怀着独立建国梦想的人民感到失望,他们要的是一个国家,不是和平或健全的经济。
西方政府主要靠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对伊斯兰国进行作战。很多库尔德人会主张他们已挣得了独立的权力。不知有多少次,我一坐进计程车就立刻听到司机宣布他是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人,还说他们和美国及以色列关系密切――很多库尔德族人喜欢以色列,因为那是一个强敌环伺、坚忍不屈的小国,就像他们一样。
「美国、以色列、库尔德斯坦!」最近有个男人这样跟我说。他伸出三根指头,然后握成拳头。 「合在一起,我们就能赢!」「赢什么?」我问。 「所有一切!」他露出灿烂的笑容。 「尤其是阿拉伯人。」他告诉我,他曾加入库尔德族反抗势力,对抗
海珊政权。他看不出海珊政权和伊斯兰国有何不同。据说伊斯兰国吸收了一些前海珊政权的军官。
「都一样、都一样,」他说。
就在伯丹.夏巴尔哲里休学参战的同时,另一位伊拉克年轻人加入了伊斯兰国。 21或22岁的萨米.海珊来自基尔库克,就在夏巴尔哲里就读大学的南边、车程不到两小时的地方,邻近的巴巴格格是主要的油田之一。他是个瘦巴巴的阿拉伯孩子,和夏巴尔哲里一样容易受别人影响,不过不管哪一位听到我这么说,可能都会觉得很受伤。萨米.海珊之所以转变成好战伊斯兰教徒,可能是因为当地教士的耳语。他或许还曾抗拒过,至少有一阵子如此。但他对未来感到绝望。伊拉克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在美国入侵之后,根本不曾体验过库尔德族人经历的那种太平盛世。在许多地方,他们过的生活悲惨得多。
当我在去年春天认识他的时候,也就是在他被捕后、失踪前,他说他是因为相信伊斯兰教遭受攻击才加入武装分子。说服他的是脸书和其他社群媒体上的宣传,以及激进教士的讲道内容。他和夏巴尔哲里一样想经历有使命感的冒险,而他也知道最终要和库尔德族人和阿拉伯同胞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但夏巴尔哲里是无神论者,萨米.海珊则视自己的选择为神意志的彰显,至少一开始是如此。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若非受到杀戮的引诱,就不可能被伊斯兰国吸引。没有谋杀、破坏、强暴及虐待,没有愤怒无情的上帝,就没有伊斯兰国。所以一个年轻人是要去捍卫一些什么,另一位则是来摧毁。
当萨米.海珊离家参战时,显然也决定不告诉母亲。数月后他在偷跑回家看她时被捕。
基尔库克是具体而微的伊拉克,在那阳光炽热的环境中,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及土库曼人――还分逊尼派、什叶派和基督徒――比邻而居。数世纪以来的多元、美好与爱恨情仇,都渗入了这片麦田连着油田的炙热平原上。 2014年6月,在伊斯兰国发动攻击之前,伊拉克军队就弃守了这座可能是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但以理安葬之地的城市。
对库尔德人来说,这感觉仿佛命定:他们长期以来相信基尔库克理应属于自己。那个6月,库尔德人只需要抵御伊斯兰国的入侵,就可以重新伸张他们对这片祖传疆域的所有权,因此满腔热忱的库尔德族士兵涌入基尔库克,填补伊拉克士兵撤退后留下的防卫空隙。
这不是件容易的任务。库尔德族自己的安全部队一开始面对了人手不足、装备不良以及未能及时针对行动迅捷的敌人调整步调等问题。伊斯兰国战士横扫了北边和东边,夺下伊拉克第二大城摩苏尔,杀死了一千多名平民。他们很快就推进到库尔德族领土,也挺进到基尔库克的郊区。
有办法的库尔德人开始准备逃走,没办法的只能想像即将降临的恐怖。但勇敢却毫无组织的军人和志愿者却紧急准备迎战敌军。他们沿着蜿蜒数百公里的库尔德区边境前线建构起零星的防御工事。自由斗士部队有时是坐计程车抵达战场,穿着网球鞋,拿着失了准头的老旧步枪。在这些前仆后继奔往前线的人当中,也有伯丹.夏巴尔哲里。
等到他率领一个由大学生年纪的志愿者组成的单位抵达基尔库克时,西方国家已出动战斗机支援库尔德族部队的行动。空中掩护让库尔德族人得以阻挡伊斯兰国战士,在某些地方甚至开始迫使敌军撤退。基尔库克暂时逃过一劫,库尔德族成为少数能对抗伊斯兰国的部队之一。
然而城外的战事却持续进行,集中在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的残破小镇。夏巴尔哲里的部队只在仓促间受过训练,大多时间也不被允许参与真正的战斗。他单位中的年轻人说他们乐意为战场上的同志做任何工作,像是煮饭和洗衣服,真的是这样――不过许多人仍梦想着要证明自己不是只能洗衣服而已。
有一次,在进攻基尔库克西南方村庄赛叶德.凯拉夫的混乱行动中,夏巴尔哲里终于有了机会。他的单位缓缓地向伊斯兰国阵地推进。乐昏了头的夏巴尔哲里拿起卖掉乌德琴买来的步枪,在一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往前冲。
一名伊斯兰国战士开始往装甲车下方射击库尔德族士兵的腿。一颗子弹钻进夏巴尔哲里的小腿。他被人拖走送上救护车,不久后库尔德族部队也全数撤退。
之后,他的父母来到医院看他。母亲哭了,父亲则气到说不出话来。冒这么大的险,为了什么?为了表示勇敢?为了爱国?为了一个根本不是国家的国家?
但后来,他的父亲穆罕默德透露,即使在医院大发雷霆时,他仍以自己的儿子为荣。
「我们都会为库尔德斯坦而战,」穆罕默德说。 「就算我们不一定相信它。」
夏巴尔哲里中枪那一天,加入伊斯兰国的阿拉伯青年萨米.海珊也在那个地区。
我在几个月后某日早上见到他,当时他刚和其他六名年轻人在基尔库克的一次警方突袭行动中被捕。我来到靠近市中心的警方基地,萨米.海珊被带到一间狭窄会客室里。他没穿鞋子,满脸怒容。萨米.海珊似乎没有受到伤害,只有拇指变了颜色――沾了用来在自白书上盖手印的墨水。
一名刑警问了萨米.海珊一连串问题,其中许多在长达数小时的审问中已回答过了。你为什么加入伊斯兰国?你们成员里有很多外国战士吗?你们捉到亚兹迪女孩后做了什么事?
这个问题指的是伊斯兰国成员对亚兹迪族群的暴行,亚兹迪是库尔德族内一支非穆斯林的民族和宗教群体――他们被伊斯兰国战士俘虏后遭受的命运震惊了全世界。这名刑警是问给我听的,目的是要我这个美国人知道我们留下伊拉克独自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恐怖暴行。
「战士抓了亚兹迪人后就为所欲为,」萨米.海珊冷冷地说。
他跟我说,他后悔加入伊斯兰国,他们承诺的荣耀和伊斯兰教真理都是空话。
「他们根本就不是穆斯林,」他说话的时候一面变换了一下坐姿,然后双眼盯着地板。
萨米.海珊只是一个光着脚丫、既疲倦又困惑的年轻人。不久后,警方指挥官、也是库尔德族将军的沙哈德.卡迪尔便带着我来到一处小庭院,那里的鲜绿草地上跪着他前一晚逮捕的其他人。他们都被蒙上眼睛、戴着手铐。
「他们会怎样?」我问将军。
「他们会坐牢,」他含糊地说,挥了挥手。 「接下来会怎样由不得我决定。」
有一个流传已久、难以忽视的流言,说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例行会处决伊斯兰国俘虏。我在离开警察局时问了问随行的翻译。
「那个孩子会怎样?」
「他当然会被处死。」
「你怎么知道?」
「老兄,你干嘛在乎?他可是伊斯兰国成员。」
真的,当时我确实只想到了萨米.海珊的母亲,不知道她究竟是否还能再见到儿子一面。
我花了几个星期时间试图找出萨米.海珊的下落。我问过警察、自由斗士指挥官、政治人物、律师、甚至库尔德族自治区的总理。没人可以――或愿意――给我任何线索。
有好一阵子,我很执着于他的案子。称不上是因为同情――对志愿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很难产生同情。但他的故事牵涉到库尔德斯坦、伊拉克及中东现在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包括如何建立并成为运作正常的国家、赢得周边国家的支持、并让国内同胞,不论是谁,都能安居乐业、不至转过头来对付你。
萨米.海珊只是成千上万名涌向伊斯兰国的人中的一个,当我找不着他时,就改找其他人。伊拉克境内有许多伊斯兰国战士是伊斯兰国在占领地区招募或征召而来的伊拉克公民。大多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也有库尔德人加入。
在库尔德斯坦的克拉迪哲市,一位名叫撒拉.拉希德的男子告诉我他18岁的小舅子赫明的故事。赫明在2014年加入伊斯兰国。这个年轻人一直定不下来,找不到稳定工作,库尔德斯坦的黄金十年并未嘉惠他。在当地一位也是库尔德族裔的伊玛目(穆斯林领袖)影响下,他逐渐变得激进,这位伊玛目讲的都是有关圣战、殉难和天堂的事。
赫明和其他几个人遵循这个人的讲道去了叙利亚,希望能对抗独裁者巴夏尔.阿塞德的军队。但伊斯兰国领袖很快就命令赫明和他的朋友们返回伊拉克,与自己的同胞作战。
拉希德藉由电话和脸书来追查小舅子的行踪,并逐渐确信他并不快乐。他加入伊斯兰国并不是要攻打库尔德人,他也似乎不再相信伊斯兰国的宣传。 2014年10月,赫明在伊斯兰国拿下的辛贾尔镇(2015年年底又被自由斗士夺回)被杀。拉希德被告知赫明是死于战斗,不过他并不相信。
「我们认为他是准备要离开达伊沙(Daesh),」他说,这是阿拉伯文中常用来称呼那个团体的名字。「因为他死的那一天辛贾尔镇根本就没有战事。我想他打算回家,他们就把他杀了。」
拉希德哀求伊斯兰国指挥官让他领回赫明的遗体,结果被拒绝,他们一家人只好靠着脸书上最后那几张照片凭吊这位面带微笑、穿着借来的迷彩服的胖男孩。
「赫明是个大男孩,」拉希德说。「许多男孩加入达伊沙不是因为他们是极端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我。我怪自己没能好好照顾他。天知道他现在会怎么样。」
拉希德指的是死后的世界,他跟我保证,赫明不会在那里找到天堂。
隔周我让伯丹.夏巴尔哲里看我帮萨米.海珊拍的照片。
「我恨他,」夏巴尔哲里说。「他让我有报复的念头。我会报复的。报复他们对我、对这里所有人的所做所为。我向你保证。」
那是一种非常库尔德式的表达方式。
10月分我最后一次造访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时,我再次寻找萨米.海珊的下落。逮捕他的那位警方指挥官已记不起他的名字,而伊拉克司法系统依旧不透露任何讯息。萨米.海珊就这么消失了,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成为过去十年、甚至50年间伊拉克境内数千名失踪人口中的又一个鬼魂。
我那些库尔德族朋友,都变得更疲惫、更忧郁了。自由斗士持续在好几个地方击退伊斯兰国,但在其他地方,伊拉克军队却节节败退。摩苏尔和拉马迪等主要城市在伊斯兰国战士的控制下民不聊生,而伊拉克的经济(也跟着影响库尔德自治区的经济)也在油价低迷和多年战事下疲弱不振。这个血迹斑斑的国家似乎没有迈向和解的迹象。
那个月,有好几个库尔德族城镇都出现示威抗议活动。大部分抗议活动还算平和――以学校老师为例,他们要求发放积欠好几个月的薪水。但其他抗议者要求政治改革,这类示威活动有些出现暴力行为,甚至造成死亡事件。在苏莱曼尼亚,身着黑色镇暴装备的警察包围了市中心的市集,连前线的自由斗士都被召回来维持秩序。入夜后,军用车队蜿蜒驶过市区。
尽管情势动荡不安,夏巴尔哲里却似乎很乐观。他最近刚回到学校,恢复全职学生身分,并把主修科目从工程改为国际研究。他已经不再想回去战场。
「政治是唯一可以带来改变的方式,」他告诉我。
我一定笑了出来,因为他突然间严肃起来。
「真的,千真万确,」他说。「在库尔德斯坦若不经由政党,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那就是我的下一个战场。」
我们走在苏莱曼尼亚市的沙林街上,只要天气不错,那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挤满库尔德族年轻人,大多是男性,他们来回走动,喝茶、打撞球、吃东西、谈笑、互传简讯直到天明。
此时的街道却出奇地安静。
「很多人都走了,」他说。我以为他指的是回家。
「不是,是去欧洲。他们变成难民了,先去土耳其,再试着到希腊或其他地方,再去德国。大家都想走。」
「为什么?」
「每个人都认为伊拉克没戏唱了,玩完了。他们也不再相信库尔德斯坦。」
我想像着人满为患的难民营,和怀抱希望的难民大量涌入在欧洲造成的混乱。如果撑得过艰困的旅程,这场出走潮从多年前就已开始,现在只是加快速度而已。
「那你呢?」我说。「你会留下吗?」
夏巴尔哲里面带笑容。「会。我就是那种库尔德人。我绝对不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