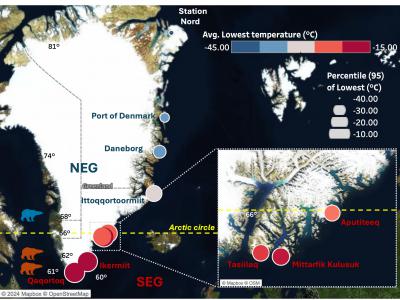野化:大自然若能自由奔放 结果可能精采绝伦
夜莺(如图中这只)正是伊莎贝拉.崔礼看到重新出现在聂普堡的生物之一。聂普堡是伦敦南部一处占地广阔的庄园,崔礼夫妻俩正透过一种名为「野化」的过程,让这片土地回归野性风貌。 PHOTOGRAPH BY LISA GEOGHEGAN, ALAMY STOCK PHOTO
所谓的「菌根真菌」和它们形成的网络,能以庞大的沟通网连结起如图中这棵欧洲山毛榉之类的许多树木。崔礼在她的书《野之生》中写道,聂普城堡的土地上冒出了兰花,是真菌网络可能又重新连结起来的象征。 PHOTOGRAPH BY YON MARSH PHOTOTRIX, ALAMY STOCK PHOTO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Simon Worrall 编译:钟慧元):所谓的野化(rewilding),是要人类不去干扰土地,让自然过程自然地发生。
英格兰南方一个慵懒的小角落里,有场革命正在进行。好几个世纪以来,聂普堡(Knepp Castle)14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贡献给了密集农业与酪农业。但到了2001年,伊莎贝拉.崔礼和她先生查理.伯勒尔(Charlie Burrell),决定卖掉乳牛、收起犁头,让大自然接手这片从18世纪晚期开始即为查理家族所有的地产。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结果。已经一个世代都没人见过的紫闪蛱蝶(Apatura iris)和夜莺等物种,又重新出现在这片从几十年来过度施肥中慢慢康复的土地,天然的河流系统也恢复了。
当国家地理找到了《野之生》(Wilding)一书的作者崔礼时,她解释了许多概念,包括「野化」一词,是要让动态的自然过程、包括消长循环直接接手;还有,地球生产的食物其实早已足够人类所需;另外,若想野化自家庭院,你能做的其实很多,就算院子小小的也可以。
「野化」这个词,可能不是所有读者都听过,可以解释一下吗?还有,你们希望在聂普堡达成什么样的理想?
聂普堡庄园是一片占地14平方公里的产业,位于西索塞克斯(West Sussex),距伦敦中心约71公里,就在整个英国最忙碌、最拥挤的地区。这里是一片小小的乡下地方,我先生在1980年代早期从他祖父母手中继承这片土地,当时这里已经密集耕作了6、70年。刚从他祖父母手上接下来时,这里是个逐渐破败的农场。我们是绿色革命的孩子,自认懂得比他们更多[笑],我们能大有所为。
我们遵循家族传统,有长达17年的光阴,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作物、饲养乳牛。每一寸能耕作的土地我们都耕作了。但到了1990年代左右,却遇上了瓶颈。我们意识到,黏土地就是无法这样密集耕作,因为黏土从来就不该密集耕作。我们的黏土每年几乎有六个月是三不管地带,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就像现在。 [笑]所以我们就设法去找些别的事情来和这片土地合作,而不是跟土地对抗。所以在2000年左右,我们展开了一项野化计画。
我们的用意是要借着这个计画,设法恢复这片地景的某些自然进程、恢复一些活力,让大自然能完全自行运作、也运作得宜。这是个非常袖手旁观的计画。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放了完全自由乱跑的动物群来驱动这个计画。就是它们创造出栖地和生物的多样性,促成了丰富多变的植被结构,而这些植被里还有其他生物在蓬勃生长。野化的关键就是要退一步,让自然过程自然地发生,这种状况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因为这些都是动态的、我们完全无法掌控。
请告诉我们聂普的老橡树如何启发了你们,而树又如何透过真菌沟通。这听起来好像电影「阿凡达」的情节喔!
[笑]我觉得「阿凡达」可能真的有深入研究过这些事呢!这些橡树让我们醍醐灌顶。我们有一棵很可爱的橡树,离城堡只有几公尺,大家都叫它「聂普的橡树」,因为它就是这么神奇的宝贝。这棵树已经500岁了,一定还曾经在英国内战期间看着圆颅党人和保皇党人经过。它根本是纪念物啊!可是这棵树却从中间开始裂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加拿大军队驻扎在这座城堡,他们尝试用坦克履带把树捆起来,其实他们弄得还不错。但60年过去了,这个做法也快不行了。
我们听说有一位很厉害的人,叫泰德.绿林(Ted Green),他是温莎大公园(Windsor Great Park)的老橡树总管。我们请他来看看这棵了不起的树,结果他说,这棵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稍微修一下枝条就好了。接着他看看身后房子周围的雷普顿公园(Repton Park)。这个地方的地况本来就已经不佳了,二次大战时,又因为要响应为国生产粮食的「为胜利翻土」运动(Dig for Victory)而开始耕作,就这样一路耕种下来。我们也继续耕作,因为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
泰德查看了这些树,有些已经有300、400岁了,他注意到我们犁田是一直犁到树干旁边。从1950年代以来,我们用的化学物质愈来愈多,我们的牛在树底下吃草,躺在树荫下休息时也直接把树根压得更密实。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在欺负这些树,让树的日子万般难过!犁田扯断了树根,因为橡树根浅,尤其又是像这样厚实的黏土区。我们还在土壤里灌满了肥料和除草剂,把什么都杀光光了。
我们不过才刚刚开始了解菌根真菌(mycorrhizal fungi)的网络,有些人认为这种网络其实可以覆盖整个大陆。这是个神奇的通讯系统,就像电脑的电路版一样,树木可以在发生攻击事件时,透过这个「电路板」送出化学讯号给附近的其他树木。这个网络不只警告同种的树木,也会警告其他种类的树,让所有树木都能巩固好自己。但我们却切断了树木的一切求生机制!
聂普的时间线和这里发生的变化非常不可思议。自从我上次拜访以后,这三年来聂普经历了一些惊人的复苏。请告诉我们夜莺的成功故事。
对!夜莺是我们的头条物种之一!我不认为有任何生态学者预见到我们能让夜莺返回这片农业化后的土地,更别说才经过这么短的时间。我们看到荆棘灌丛冒出头来,而夜莺最爱的就是荆棘灌丛了! 2002年,我们连一只夜莺都没有;到了2012年已经变成32只。是32只唱歌的雄鸟耶!
我们现在是全英国夜莺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夜莺的数量从1960年代开始已经下跌了90%。夜莺是极危的鸟种,总的来说有可能会从英国消失。如今已经没有荆棘灌丛了,但夜莺就是爱待在荆棘灌丛里。
英国的粮食自给率从1980年代的80%跌落到62%,预计到了2040年,会跌落到53%。如果每个人都让自家土地重新野化,会不会出现食物危机?
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经济的时代,我们喜欢酪梨、香蕉和非当季生产的番茄。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活动食物市场在全球各地移动。无论是好是坏,这样的状况大致是由消费者所造就的。如果我们只求自给自足,那能吃的食物会减少非常多。我们就只好回头吃芜菁马铃薯泥和羊肉了[笑]。在这种考量背后,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基本事实,那就是以全球角度来看,我们生产的食物足够110亿人口食用,但其实现在只有约70亿人口。有了现代科技的奇迹,目前人类用于食物生产的土地比以往都少,但我们生产出来的食物,却是前所未有地多,这正是大自然的天赐良机。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所有土地都野化。但野化提供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机会,可以把不具农业生产力的土地用于生态系服务,这些服务包括物种多样性、还有农业所依赖的授粉生物,而我们也都知道目前受粉生物正面临危机。如果我们想看到人类在面临气候变迁和愈来愈严重的污染时还能存活,就需要让生态环境能迅速恢复。唯有这些孤立的小面积自然环境都连结在一起,才可能做到这一点。野化能创造出串连起整个环境的走廊和踏脚石。
水灾会对社区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你们在聂普堡的保育行动也包括了野化河流和湖泊,这对保护周围社区有什么帮助?你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野化也通常能预防水灾?
我们野化了流经我们土地、约2.8公里的阿杜尔河(Adur River)。这其实是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导入运河的一条小溪,因为当年那些人希望尽快把水引出土地,才好把每一寸土地都拿来种食物。不过,他们也不算真正成功,因为我们的土地湿到夸张,尤其是那片草泽地(water meadow)。经过跟环境单位八年的官僚角力之后,我们的目标终于得到他们的支持,把河流推回原本的泛滥平原。
我们填平人工水道,现在溪水恢复成原本的泛滥曲流(meanders)。天降暴雨的时候,雨水不再冲进如高速公路般的人工水道、直接奔向大海,并顺路冲走桥梁、灌满涵洞和排水沟。如今草泽发挥了原本应有的功能,吸收雨水,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几星期中慢慢释放,这样就再也不会出现暴洪。就算碰到干旱,水分还是会经由土壤结构的这种海绵效果慢慢释放出来。
我们也准备要申请许可、野放海狸。田野间有海狸的例子真的是太震撼了。我们看过的地方,不只北美洲、包括在欧洲重新野放海狸都非常成功。它们对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都有不可思议的正面影响,尤其是在河流源头处和有泛滥倾向的地区。海狸扮演的角色就是神奇的水利工程师,建造出能避免泛滥的结构。它们是我们缺失了好几个世纪的神奇关键物种(keystone species)。
野化在你家土地上所达成的效果、还有你在碳封存(carbon sequestration)方面的发现,都让我赞叹不已,请为我们解说。
目前农业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土壤结构的破坏。我们耕了又耕、犁了又犁,因为有化学肥料的「魔术」,所以我们过去并不需要考虑土壤结构的重要性。根据估计,英国的土地上或许只能再收获100次,然后就没有东西可以种了!在聂普,我们看到微生物又出现在土壤里,我们有粪金龟把便便拖进土里、田间也有蚯蚓,我们还在耕作的时候,这些田地根本就可以算是生物灭绝了。我们也认为菌根网络正在慢慢重建,因为我们发现田野中长出了野生兰,而野生兰是非常棒的菌根真菌指标。如果你有土地是永久性的牧草地,上面又没有栽种农作物,那这个地方的碳封存效率也会很棒。这又是野化所提供的另外一种生态系服务。
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14平方公里的庄园和一座城堡;其他人如果想协助野化、复育土壤,又该怎么做?
说到野化,我们讲的是生态过程,是一种动力论(dynamism)。规模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大自然才能重新开始动态运作。一切都跟土地的状况、经历和所在位置有关。我去荷兰看过一个野化计画,那里才1.4平方公里大,只引入了少数野牛和柯尼克马(Konik pony),这些动物就修复了这个极为脆弱的沙丘生态系。
不是只有在非常大的地方,才能发生神奇的事情。我们也看过只拥有小片土地的农夫聚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把彼此土地间的围篱拆下,共同打造一个野化计画。就算你只有一小片地在某处,甚至只是家里的后院,你能做的也很多。跟当地的野生动物信托聊聊,看看你的土地是否可以跟别人的土地连结起来,成为连接到另一处自然保留地的踏脚石。如果你有一棵树,要让死木继续留在树下,这样才会变成无脊椎动物的栖地。庭院的草不要剪短、更绝对不能使用化学药剂。一定要有机!在这个连结之网里,每个人都能发挥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