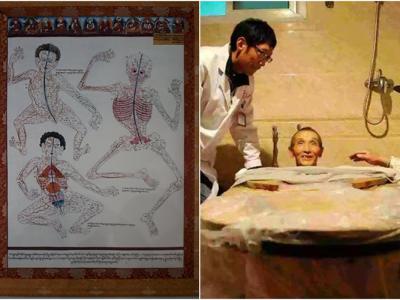拥有1400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是连接中国南北的伟大工程
驳船自古以来就往返于1800公里长的运河上,连接了北京与耀眼的南方终点站杭州。新建的仿古寺庙是水岸活化计画的一部分。
微山湖是运河系统的一部分,湖上一名渔夫正把鸬鹚抓到船上。当地仍有少数家庭延续着祖先一千多年来的谋生方式,用绳子绑住鸟的脖子,使它们无法把较大的鱼吞下肚,然后再逼它们把抓到的鱼吐出来。
在淮安的淮钢钢铁公司,平板卡车上的钢条将被装载到驳船上,经由运河运送。每年都有大约4亿公吨的煤炭、砖块、谷物和其他货物沿着这条水道在杭州和济宁之间的各个点移动。济宁以北的河道则大部分都已经干枯。
苏州昆剧院的名角正准备排演。昆剧是一种风格化的艺术形式,讲究音乐、唱词与舞蹈的和谐融合,于1500年代在运河畔的苏州及其周边地区兴起。表演者经由水路将昆曲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
运河沿岸的村庄反映出中国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拉锯。在微山湖边的渔村下辛庄,23岁的准新娘魏莉身穿传统的红色嫁衣。未来新房墙上的结婚照是几星期前拍的,照片中的她穿的是西式婚纱。
以水为家曾经是大运河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对这对母女来说,至今依然如此,她们将必需品从岸上带回家,而她们的家就是施桥镇上一艘除役的水泥驳船。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观光客而整顿运河,已使这样的水上人家慢慢消失。
一名年轻人一大早就赶着鹅群去觅食,接着再把它们赶到淮安南边的运河去游水。在运河沿岸的农村里,很多小农的谋生方式就是为船员供应水禽与肉品──还有香烟和啤酒。
在这张未曾发表过的照片里,1940年代大运河上的生活步调显得十分悠闲。
修复后的水都周庄打着「东方威尼斯」的招牌,每年吸引超过250万游客。
杭州的北新桥码头上,每一名挑夫都担着约90公斤重的砖块。挑夫一词的由来,是因为他们用手工制的竹扁担挑运货物。在运河沿岸的大部分地区,人力已被吊车和卡车取代。
渔人在海河上捕鱼,一旁就是天津之眼摩天轮。为了吸引观光客,有一段运河被修复,并且引入了流经天津的海河之水。 Photograph by Michael Yamashita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拥有1400年历史的大运河是连接中国南北的伟大工程,至今仍在使用中。
大运河上的驳船没有花俏的名字,船首没有美人鱼雕像,船尾也没有漆上陈腐的格言。倒是船的侧边印有文字和数字,像是牛只身上的烙印。这么不带感情的态度或许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无足轻重,但14个世纪以来,航行在大运河上的驳船将中国紧密连结在一起,承载着谷物、士兵与思想,往返于南部的经济腹地与北部的政治首府之间。
在北方的济宁城外,人称老朱的朱思雷发动他崭新的「鲁-济宁-货3307号」驳船上的两具柴油引擎。时间是清晨4点半,老朱想趁其他人还慢条斯理地准备起锚时抢先出发。可是当我注视河岸时,却发现在逐渐泛白的天空底下,树木已经不再往后退。从另一侧的窗户看出去,我惊讶地发现其他驳船一艘艘超越了我们。这时无线电劈哩啪啪地传出了声音。
「老朱,怎么搞的?」一个船长笑着说。 「你错过航道啦!」
原来我们搁浅了。老朱一脸嫌恶地眯起眼睛。建造这艘驳船时,他已经花了六个月在陆地上监工,现在一急之下,他却低估了大运河强劲的水流和容易淤塞的航道。他不情愿地拿起麦克风征询意见。
得知沙洲很小后,他专注地盯着河水看,决定立即行动。他用力倒档,将油门催到底。柴油引擎猛然一抖,50公尺长的驳船和船上1000公吨的煤炭也跟着摇晃。他转动舵轮,迅速换档,再次把油门推到底。我们向前猛冲出去,掀起阵阵浪花。为了省电,船尾灯被关掉,只有月光照亮水面,「鲁-济宁-货3307号」就像一艘潜水艇,朝着敌营前进。我们的目标:南方690公里外的南通。
理论上,大运河的总长是1800公里,连接北京与南方大城杭州。但过去将近40年来,水道的上半部──也就是从北京到济宁的河段──已经过于干枯,无法航行。如今水道的主要商业干道长523公里,由济宁通往长江。
最早的运河系统由隋炀帝下令开凿,中国历史学家视之为杰出的疯狂之举。古代中国的主要河川都是由西向东流,而隋炀帝想要打破这项地理限制。他必须设法将长江流域富饶之地的稻米运往西北方,喂养他的宫廷,更重要的是喂养他那些永远都在与游牧民族打仗的军队。因此隋炀帝的官员强征了估计有百万民工,大多是农民,开凿运河的第一段。在数以千计的士兵监督之下,男女工人日以继夜地赶工。九世纪时,唐末诗人皮日休写道:「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根据官方说法,大运河于公元605年完工,耗时171天。但事实上,这项工程却是花了六年,而且夺去无数人命──其中许多是饿死的农村人民,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收割作物。
大运河不只是运送粮食而已。作为统合国土的地理特征,它既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也是入侵者的战略目标。 1840年代初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想钳制中国,于是占领位在大运河与长江交会处的镇江,封锁了往北京的漕运与税赋。不出几个星期,中国就投降了。
大运河也是文化通道。到大运河巡视水闸与堤防的皇帝会观察并吸收当地文化。据说北京有两大招牌特色就是这么来的:一是来自山东的北京烤鸭,另一是来自安徽与湖北的京剧。仰赖大运河四处巡回的戏班子对着码头祈福,诗人则因大运河而诗情迸发。唐代诗人张继曾以河畔的寒山寺入诗,写下「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名句。
以大运河为家的船民,在要价10万美金的驳船上重现农村生活。每艘船上的船员人数都不多(通常只有一家人),和收割期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黑了就把船一艘挨着一艘系好。老朱的太太黄希玲现在站在船尾,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先前的驳船上出生的。她负责烧饭打扫,将小小的船舱打造成遮风蔽雨、抵挡日晒的窝。 「男人说船只是讨生活用的,但我们一辈子都在船上过,」她说。 「有太多回忆了。」
老朱夫妇的大儿子朱强最近接手了他们的上一艘驳船。小儿子朱庚鹏今年19岁,外号小朱,现在在这艘新驳船上工作,老朱正在训练他当船长。小朱很照顾我,会将他父亲难懂的山东口音翻译给我听,并注意不让我掉进水里。他还在我的防水门上方用毛笔写下「私人卧铺」,为我的舱房增色不少。 (在两个空的油漆桶上铺一块木板,加一条被子,储藏室就摇身变成了我的豪华客房。)
小朱的样子不太像船民。他留着潇洒的小胡子,顶着永远像刚睡醒的乱发,身穿一件毛皮镶边的紫色外套,看起来跟中国省城里的时髦小伙子没什么两样。他受过中学教育,驳船停在闸口时,都是由小朱上岸跟官员交涉。 (老朱虽然才46岁,却是文盲。)休息的时候,小朱似乎都在跟女朋友传简讯,她在济宁的一家面包店工作。他打算在结婚以后把她带上船,一起住在位于船头的房间里。
「对她来说可能会很辛苦,因为她不是船民,」黄希玲说。 「但她是个好姑娘。很勤快。」
船民很少放纵自己。他们都活得精打细算,一个家庭会致富还是会破产,就取决于这样的算计。第一天结束时我就领悟到这一点。当时我正在跟老朱的同乡郑成芳聊天。我们的船系在一起,于是我跳过去和他闲聊。我们看着老朱刚上过新漆、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船时,我说,这景色不是很美吗?
「不不不,你不了解我们,」他冲口而出。 「这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我们船民没有船就活不下去。」
郑先生陪我回到我们船上,跟老朱抽根烟,黄希玲则准备简单的晚餐,有咸鱼、米饭、炒青菜。 「你若要报导我们的事,就得知道点别的,」郑先生说。 「我们船民凡事只有接受的份儿。煤老板定价格,放贷的定利息,政府官员定各种费用。我们只能点头,继续埋头干活儿。」
这是船东之间不变的牢骚:跟田里的农夫一样,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农民看天吃饭,船民面对的则是阴晴不定的官僚和难以预测的经济。他们必须根据各种因素做出复杂的决定,从全球商品价格走势到中国金融改革都要考虑进去。确实,郑先生滔滔不绝的同时,老朱始终盯着关于中东与油价的电视新闻。 「你怎么看?」他问我,打断了郑先生的话。 「油价会涨破一桶100美金吗?钢价呢?」
老朱借了一大笔钱。他的驳船负载量是1200公吨,但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济宁的煤炭中间商只能供应1100公吨。老朱从前一吨可以卖到70元人民币,如今却只能卖45元。这表示他这一趟的总收入是4万9500元人民币。柴油大概要花2万4500元,运河的港务费则超过1万元。此外还有各式罚金,从排放废水到照明设备不合格都有。如果顺利,他可以净赚5000元。但这还没扣除船贷利息。为了买船,老朱向高利贷借了84万元,利息15%。光是这一趟,利息就高达1万500元。整体而言,「鲁-济宁-货3307号」的处女航大概会让他赔个5000元。
不过老朱相信经济衰退已经在2009年达到谷底,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建造现在这艘船。他也相信钢价会上涨,因此相较于以后造的船,他的船会显得造价很便宜。他也认为煤价会回升。 「我会赔个五年,之后就没事了,」他信心满满地说,就像个看好全球经济复苏而建立多头部位的华尔街交易商。
两星期的行程走到一半时,我们抵达扬州。船只突突驶过仿佛用绿色颜料干笔画过的杨柳,以及点染着紫花、红花与黄花的原野。正是唐朝诗人李白笔下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我跟老朱一起在驾驶舱里坐了好几个小时,看着田园风光逐渐被水泥高塔上新起的高架桥取代。
航过某个河湾时,老朱唤醒了我的白日梦。 「那是旧的大运河,或者应该说是还剩下来的旧河段,」他说着指向一条大约五公尺宽的航道,从一座小岛与河岸之间蜿蜒而过。曾经,大运河的河道是一连串曲折的弯道,南来北往的船只必须呈之字形前进。大运河拓宽取直之后,这些弯道有的变成副航道,有的则变成牛轭湖。
「很辛苦的,我告诉你,」老朱嘶哑的声音变得激动。 「你四面八方都有船开过来,时时刻刻都得小心。」他是熟悉古运河的最后一代船民,知道哪里有大大小小的漩涡,可以推动驳船──或造成船只在沙洲搁浅。在我看来,大运河真正神奇的地方似乎不在于它本身的结构,而是在于船民,他们与水道的关系超越了一切变化。
那天晚上,我们停靠在扬州郊区。在唐朝和清初这两个黄金时代,扬州就如同今日的上海。在现今繁荣的南方,财库饱满的地方政府美化了大运河并且从中获利,想借此促进观光业与房地产开发。但美化也可能造成破坏:虽然扬州将滨水区变成一座公园,有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水泥凉亭,是拥挤的城市里一片宜人的绿地,但改建工程却把运河边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夷为平地。好几世纪以来,大运河都是城市的心脏;如今它却只是个背景。
更往南方的城市,例如镇江、无锡、杭州,情况更糟糕。大运河依然通过杭州的工业中心,但除了优雅的拱宸桥以外,紧邻着大运河的所有建筑物──每一个古老的码头、仓库、系泊区──都被铲除了。 「传统上,我们都说大运河沿岸有18座大城,各有各的风味,」曾任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副馆长的周新华告诉我。 「但现在它们全都一个样:千人一面。」
2005年,地方上几位著名的艺文界人士出面呼吁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每个世代都希望下一代可以了解他们那一代,可以看到他们那一代的伟大建筑,」合写提议案的雕刻家朱炳仁在访谈中这么告诉我。 「但我们若将前人的作品都摧毁,后世又会怎么看我们?」
第八天的黎明时分,我们向东转入长江。高耸的远洋船只让我们相形渺小,激起的余波溅湿了我们的甲板。 「长江就像高速公路,我们就像一台小车,所以要小心走、尽快离开,」老朱说。三天之内,我们就抵达了目的地:南通肥料厂。由于大雨的缘故,光是卸货就花了四天,随着起重机将煤铲下船,船身也微微上升。接着老朱匆匆离开,沿着长江把船开回了运河上。
在扬州附近的小湾停泊一晚后,大家黎明即起,准备开船。小朱揉着惺忪的睡眼,松开船首的粗缆绳。老朱发动电动绞盘收锚。黄希玲解开船尾的缆绳,站在那儿监看。一股微弱的水流把我们带离了杨柳岸,将船尾推进运河。驳船朝错误的方向滑出水面时,老朱从绞盘处走向驾驶舱,平静地点燃一根烟,然后按下开关,双柴油引擎又隆隆响起。
他几乎头也不回地将船掉头驶入主航道,透过这样的大胆之举宣告:这条运河你们能走,我也可以。其他驳船不断驶近中,他将船头转向上游。接着,张力十足地停顿了一秒之后,老朱将油门推到底。引擎猛冲,螺桨打进水面,青绿色的「鲁-济宁-货3307号」在柔和的春光中熠熠生辉,加入了大运河上川流不息的船队。
撰文:伊恩‧强森(Ian Johnson)
摄影:麦可‧山下(Michael Yamash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