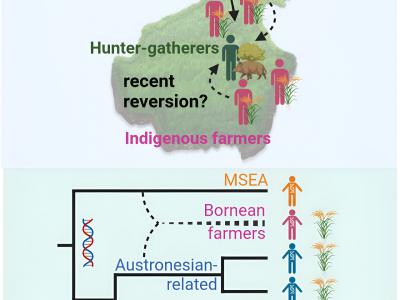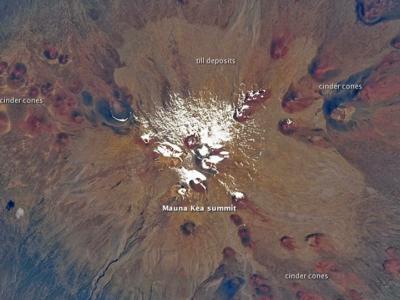神秘的成吉思汗守陵人
清政府继续免除达尔扈特人的兵役和赋税,同时规定每户达尔扈特每年筹措一两银子,用于祭祀,需要更多费用时,以募化形式解决。从1696年到1949年,253年,达尔扈特人的500两银子从没有少交过,实在不够用,他们就出门远行,四处募化。募化客观上补充了祭祀资金的缺口,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也让远方的蒙古族同胞知道在鄂尔多斯依然供奉着他们的圣主。1915年的一天,一位叫张相文的学者来到鄂尔多斯,偶然在蒙古王爷家中见到了募化的情景:募化者随身携带成吉思汗画像,手持一柄小型剑和一件祭器,口念《伊金颂》和《苏勒德颂》,让主人向圣主画像叩头供奉。这次邂逅,让隐秘的成陵露出真容,外界的人们第一次获悉传闻中的成陵原来真实存在。
重组500户后,守陵的各项规章更加严格了,比如值勤人员需持“日岗”、“夜岗”字样的牌子,不换牌以没有上岗论处。守夜为站立岗,每刻钟要打钹一次,丝毫不得怠慢,稍有马虎,就要挨鞭子或罚没一头大畜。据说,上世纪30年代末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达尔扈特,令他惊讶的是,近20年间因为误钹而挨过鞭子的只有一人。
新制度也让八白宫的神物最终确定下来,而苏勒德因其特殊地位,被单独建坛供奉,于是,达尔扈特有了左、右之分。右翼达尔扈特也叫圣主达尔扈特,负责八白宫祭祀;左翼达尔扈特也叫苏勒德达尔扈特,负责苏勒德祭祀。右翼达尔扈特多以博斡儿出的后裔为主,左翼达尔扈特则主要出自木华黎之后。木华黎与博斡儿出同为成吉思汗的左膀右臂。相应地,左翼达尔扈特也设有八大亚门特,只是称呼不同而已。班泽尔的身份为宰相,相当于苏勒德祭祀的大总管,到他这辈,已经是家族第38代传人了。
班泽尔的父亲、今年93岁的嘎尔迪是健在的年岁最长的亚门特。在巴音昌霍格草原深处,我们见到了这位受人尊敬的长者。
这是一所半新的普通红砖瓦房,你可以说它是一室一厅,外带一间厨房。屋内陈设简单,却透着一种殷实,最为醒目的是客厅南墙上的毛主席和成吉思汗画像,两位伟人一上一下,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前方。草原上但凡有人家,就必有成吉思汗画像。
自从形成伊金霍洛禁地之后,达尔扈特人基本上不再游牧,泥土房代替了蒙古包,经济条件改善之后,大部分牧民又都盖起了砖房。近几年,鄂尔多斯草原实行牲畜围栏圈养,以遏制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老人家里养有百余只羊,除此而外,还种有一片松树苗。
老“宰相”身体硬朗,思维敏捷。还在稚气未脱的时候,他就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将来会去守陵。父亲给他讲祭祀的知识,教他背诵祭文,两三万字的祭文,全靠心领神会,死记硬背。那些功课常常在清晨或夜阑人静时进行,因为达尔扈特人视祭祀为“天机绝密”,不可外泄,即使同为亚门特,彼此之间也互不交流。
“成为祭师之前,必须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献哈达、献神灯和献全羊,每个程序都有规矩,比如说全羊的摆放,得根据羊的身体结构,摆出整只羊的形状来,学会这些才能上岗。”老人13岁进入陵宫,一呆就是六七十年。眼下退休在家,但每天家中的祭拜没有放弃,遇有大的祭祀活动,他还会亲自前往,参与指导。
算上班泽尔,老人膝下共有8个子女,班泽尔虽排行老大,但继承亚门特的人并不一定非他莫属,能否胜任还要看能力和品行。以前,继承者必须得到济农(专管祭祀的地方官员)的认可,如今则需经过成陵管理局的审核。没有继位的兄弟,自然也就不属于达尔扈特的核心成员,像普通人一样,从事着各种职业:放牧、务农、当工人、做教师……斑泽尔的两个弟弟,一个在镇政府工作,一个做交警。
“一旦需要,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一个达尔扈特人都会召之即来。”斑泽尔说,“先人们祖祖辈辈都这么忠诚,一代代传下来,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断送。”同样的话,我们在鄂尔多斯听到过不止一次。
永远的长明灯,永远的戴孝人,永远的守护者—这是外人对达尔扈特的印象,也是达尔扈特人给自己的定位,如果为他们画一幅肖像,忠、义、勇、情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
达尔扈特人因忠勇而聚在一起,也许他们并不曾意识到,在他们例行公事般地忠于职守、践约诺言的同时,也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
“由于鄂尔多斯部及其达尔扈特人出自蒙古精英阶层,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黄金家族的重托,因而从其传承的文化层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贵的文化属性,既是蒙古帝王的宫廷文化,也是蒙古民族最高的祭祀文化,代表了古代蒙古文化的精髓。”内蒙古大学教授马冀认为,达尔扈特人是“研究蒙元文化的活化石”,他们对于成吉思汗文化的贡献“不可估量”。
“成吉思汗文化”是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不仅仅是对成吉思汗本人的评价和研究,它涵盖了一切围绕成吉思汗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文化概念里,达尔扈特的作用突出地体现于祭祀方面。
祭祀常年不断,有日祭、月祭、年祭和四时大祭,各种形式的祭祀中,尤以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的春祭最为隆重。今年的春祭日恰好搭上“五一”黄金周的末班车。
原以为那会是一个人头攒动、万众跪拜,如穆斯林麦加朝圣一般的壮观场面,结果却与想象中的大不一样。从清晨到日暮,虽人潮涌动,但气氛欢快而祥和,相形之下,整个祭祀更像蒙古民族的一次群众性大集会。这一天,蒙古人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云集到成陵,巴音昌霍格草滩帐篷林立,人欢马叫,赛马、摔跤、射箭……一派欢腾;这一天,在成陵只能听到一种语言:蒙语。
当日的活动因时辰而不同。上午是以家庭、团体为单位的小祭。供奉成吉思汗与夫人的白色灵包前,人们隔着几案敬献哈达、酥油及茶酒,祭师手托长明灯为其祝福,然后众人共饮一碗白酒,整个过程不足十分钟。一拨人退下,又一拨人上去,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有许多戴着红领巾的少年,他们显然是学校组织来的。
下午是金殿大祭和鲜奶祭。鲜奶祭为一天中的高潮,在位于陵园东侧的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举行,这里拴着几匹白色母马,母马的乳汁即被用来祭洒苍天。
据史料载,成吉思汗50岁那年碰上罕见荒年,借助占卜得知春三月是其主凶,于是择定三月二十一日这天以99匹白母马的乳汁,向无上苍天献祭,祈求保佑。这个仪式被保留下来,忽必烈钦定四时大典,更将三月二十一日定为春祭日,古老的祭天习俗遂成庆典。
敖包旁,一匹白马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它毛色光滑,全身雪白,神情俊逸而潇洒,既不披金,也不挂银,由人牵着,气宇轩昂地站在那里。开始,我以为它不过是一匹良驹,像在许多公园或景点司空见惯的动物一样,供人观赏和娱乐。待看到人们一个个匍匐在它的脚下,虔诚之至地向它顶礼膜拜时,我收敛了笑容:究竟是怎样一匹马,何以受到如此礼遇?
“那是成吉思汗的神马。”一位年轻的达尔扈特告诉我。
“这一匹是神马的后代吗?”我有些讶异。
“不,神马是选出来的。”年轻人说神马挑选的条件非常苛刻,必须眼睛乌亮,蹄子漆黑,全身毛银白色,没有一绺杂毛,像转世灵童一样转世而来。
他的话愈发激起了我们的兴致,进一步追问,他莞而一笑,说:“我们有规矩,许多事是不能随便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