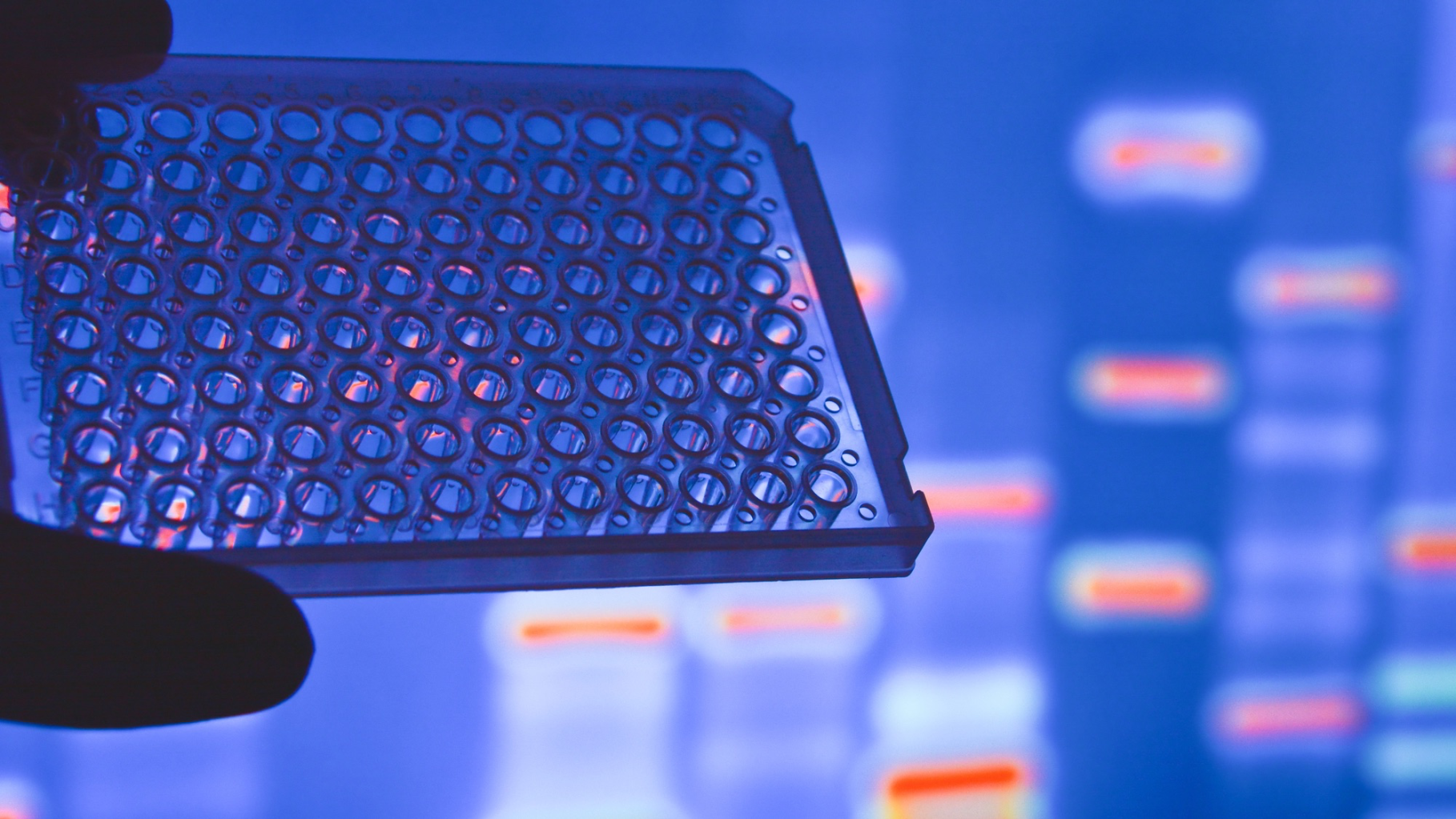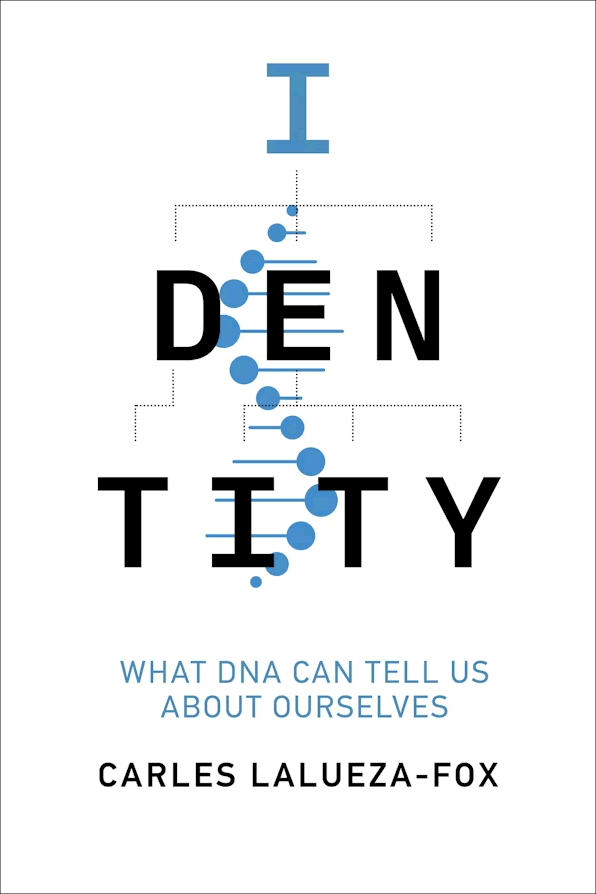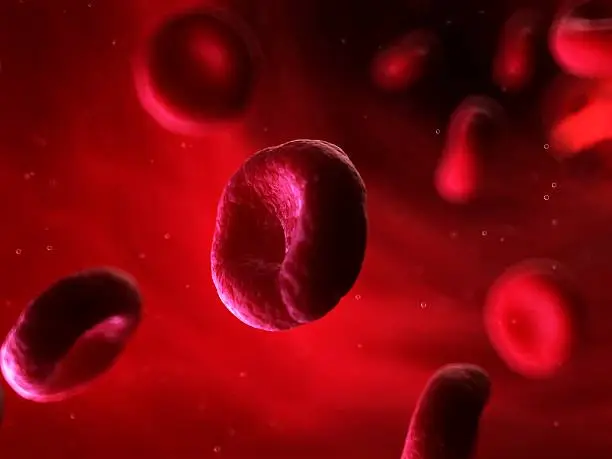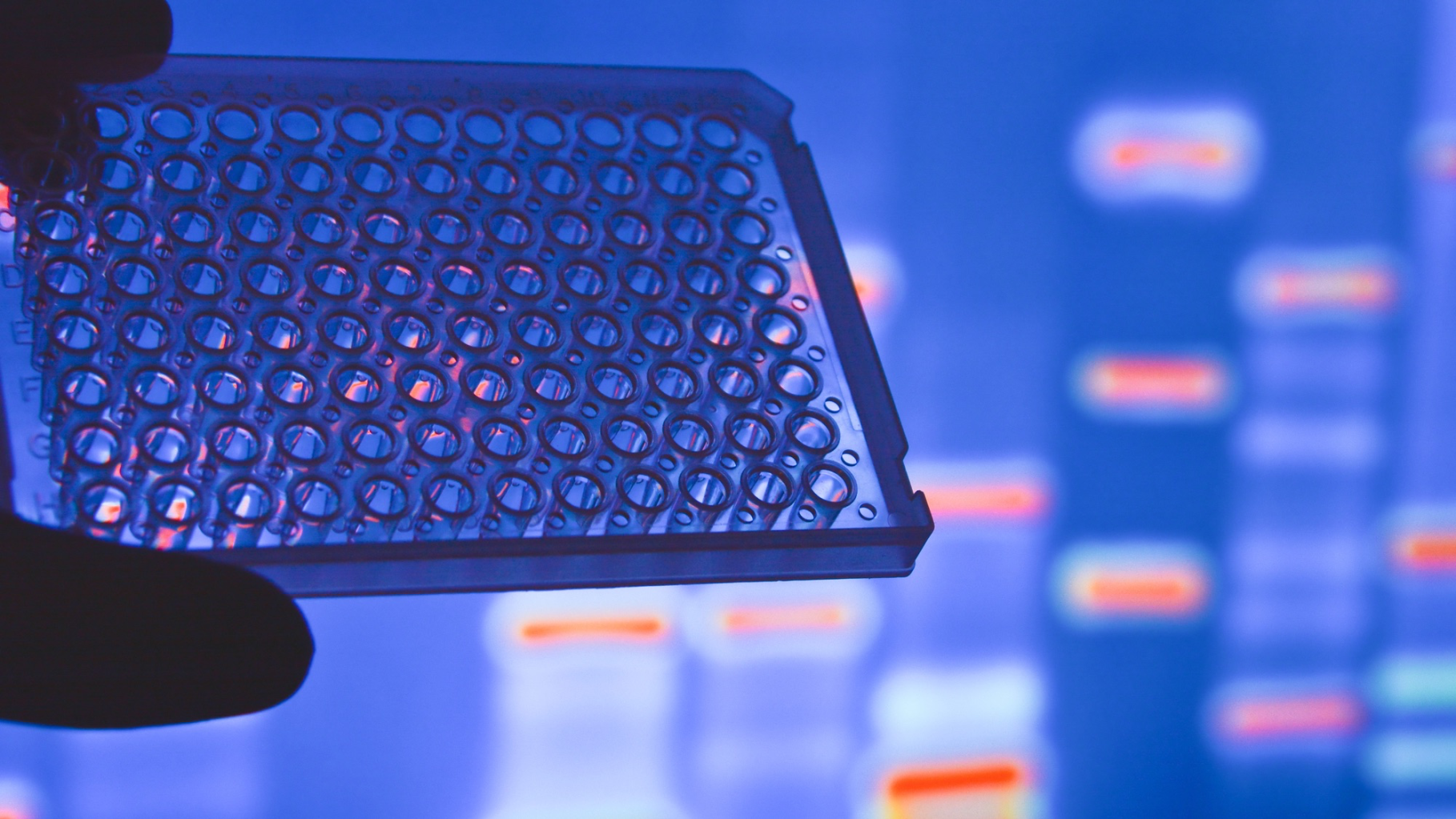遗传血统并不能说明你的全部情况
基因祖源检测,比如23andMe和 Ancestry.com 所做的,比看起来更复杂。 图片来源:uux.cn/DepositPhotos
(神秘的地球uux.cn)据MIT新闻阅读器(卡尔斯·拉卢埃萨-福克斯 /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本文改编自卡尔斯·拉卢埃萨-福克斯的《身份:DNA能告诉我们关于自我的什么》一文。
遗传祖源是一个长期以来吸引人们想象力的概念。难怪23andMe和 Ancestry.com 这样的公司把它变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基因检测的客户现在可以高兴地得知自己是“南欧人”、“东亚人”、“英属爱尔兰人”、“希腊和巴尔干人”或“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另一些人可能对他们“维京”或“亚姆纳亚”根源的说法感到着迷,发现后便相信这些启示是他们身份的核心。
然而,令人不快的事实是,这些标签和身份在历史、文化甚至基因层面上大多毫无意义。在维京人的基因组中发现祖先并不意味着你“部分维京人”。原因很简单:群体遗传学并非完美的科学。
我们所说的“祖源”只是对特定参考人群遗传相似性的近似。这些参考群体是科学家用来建模的人工构造。它们通常基于不同考古和年代的古代基因组,旨在代表特定人群(例如,“草原游牧民族”、“罗马人”、“斯拉夫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但这些标签既非普遍也非客观;它们是任意选择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分析结果的感知。
这类分类最显著的问题或许在于它们忽视了过去几百年人类流动性带来的深远影响,造成了基因固执的印象。这些分类表明,人类群体在整个世界历史中一直保持原位,使每个群体能够发展出高度不同的基因组合。
然而,古代基因组学表明,迁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持续不断。从6万至7万年前的非洲外迁徙,到16世纪开始的大西洋奴隶贸易th世纪以来,流动性——而非孤立——一直是常态。由于这种迁移和混合,与当代特定国家的个人的地理联系可能具有误导性。因此,基因相似性可能反映了数百甚至数千年前的共同祖先,而这些地区与今天生活的地区相距甚远。
在他的新书《卡尔斯·拉卢埃萨-福克斯》中,他探讨了基因检测如何提升我们对人类物种的理解。图片来源:uux.c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乍一看,人类似乎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物种。我们在肤色、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头发和眼睛颜色、身高、体重、四肢长度、脸型和抗病能力等方面各不相同。
然而,尽管我们有明显的差异,你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是世界上最不多样化的物种之一。人类共享约99.9%的基因组,这意味着两个随机选中的个体在基因组化学构成中差异极其微小。由于这种极其相似的关系,定义什么构成人口并不容易。边界可以扩展或收缩,这使得这一概念极难客观界定。
在群体遗传学中,群体被定义为一群彼此交配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群体不同的个体。这些群体有时会因其文化或地理特征而被特征所描述(例如,他们与邻近群体讲不同的语言,或被限制在某个岛屿或国家边界内)。
然而,在人类的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孤立的种群。出于实际原因,一些科学家选择仅研究国籍,而另一些则专注于文化属性。但每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想象一下,将来自相对较小且同质化的冰岛个体与地理广阔且多样化的俄罗斯进行比较。)最终,不同的群体定义取决于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审查的遗传数据。
在自然界中,存在明确定义的遗传种群。这是因为存在地理限制的种群或物种,完全与其他群体隔离。例子包括马达加斯加狐猴和毛里求斯已灭绝的渡渡鸟。在这些被称为“特有性”的情况下,物种的最大种群定义了其分布范围。
然而,在现代人类中几乎找不到这种现象;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族谱联系,追溯我们的祖先。虽然人类在过去数万年里适应了特定的环境条件——产生了皮肤色素或病原体抗性基因等特征的地理变异模式——但这种模式化只是幻觉。
例如,种族这一概念本身源自色素沉着基因,而色素沉着基因仅因全球人口分布方式而显现。但基因组学研究已证伪这些明显模式。事实上,全基因组分析显示地区间的变异是渐进的,而非固定的种族类别。
在遗传学中,科学家必须分析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人的基因组,每个人携带数百万个变异。数据量难以想象。这也引出了遗传祖源研究中的另一个核心盲点:作为科学家,我们如何想象人类遗传变异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
传统的表述,如系统发育遗传树,未能揭示这一人类遗传学的关键方面。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些群体标签逐渐被放弃:根据《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档案,论文中“高加索人”的使用率从20岁中期的12%下降th10世纪降至21世纪初不到1%圣世纪。随着这一下降,欧洲大陆标签的使用率也有所增加——例如,“欧洲人”一词的使用率在2009年至2018年间激增至42%。
最近,遗传学家提出将遗传祖先表示为重叠的圆圈,而非树状结构。例如,遗传学家詹姆斯·基钦斯和格雷厄姆·库普从大约29亿个可测量核苷酸位点开始,这些位点在人类基因组中可能变化,分析了美洲609个个体样本,仅发现3900万个可观察变异。如果分析范围限制在被定义为“常见”的遗传变异,位点数量减少到1000万个,几乎是潜在普遍数字中的微不足道一部分。
研究人员在不同人群中重复了这一方法,结果相对于总基因组长度,变量位点极少。例如,99名具有北欧和西欧血统的犹他州居民表现出5,726,377个变异,而来自巴巴多斯的96个非洲加勒比人则显示了8,018,649个(后者很可能反映了非洲更广泛的遗传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跨群体,共同变异的重叠程度极高,这意味着人类群体中几乎没有专属的遗传变异。事实上,在某一地理区域内常见的变异通常并不局限于该区域;它们在全球其他群体中以相似的频率存在。
这一切都说明,祖先和群体差异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削弱了种族作为真实生物学类别的观念。人们在社区中并不共享单一、统一的遗传背景。相反,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群体,祖先成分的比例略有不同。
与其想象过去人口的抽象模型,古代遗传学允许我们指代特定遗址和考古时期,这些遗骸来自哪些特定时期。遗传祖先并不是身份的决定性标志;它只是更大谜题的一部分,我认为为思考我们的集体身份和共同过去提供了更丰富的基础。
Carles Lalueza-Fox 是古代基因组提取和分析领域的顶尖研究专家,研究对象包括灭绝的古人类、过去的人类种群和病原体。他是巴塞罗那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著有多本书籍,其中包括《身份:DNA 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事》,本文即改编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