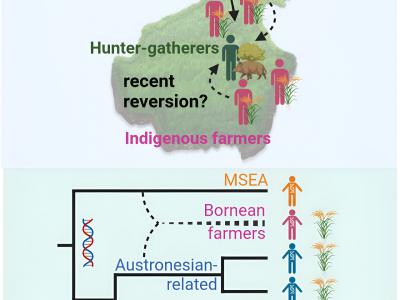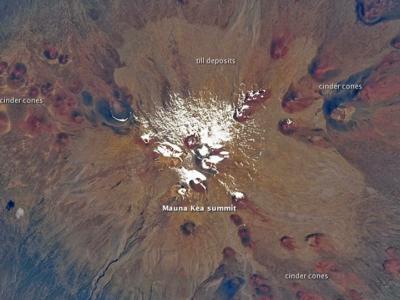神秘的成吉思汗守陵人
鄂尔多斯草原多风,大风起兮,在无遮无拦的原野上,犹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横扫一切。虽已入夏,有风的天气还是让人感到些许凉意。呼啸的晨风中,班泽尔打开祭坛上的铜庙,取出酥油灯,置于庙前的供几上,再将香炉燃起,随着苍凉的螺号声,他盘腿坐在香炉前的毡垫上,诵经一般念起颂词,另一位祭师则转着祭坛,将茶水洒向天空……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风很大,隔着灯罩,酥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跃动着。见此情状,祭拜完毕,班泽尔赶紧将灯送回庙内。“让圣主灵前的神灯永远长明是我们守陵人的责任,它已经整整燃烧780年了。”班泽尔一边整理铜庙内的神物,一边回答我的问话。铜庙不大,仅容两人,我被挡在了门外,除了祭师,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走进铜庙。
铜庙背后,矗立着五杆军旗,中间一杆高丈余,配有一枚乌金的矛形旗顶,缀以三尺长的黑马鬃缨。这个矛形旗顶蒙语呼作“苏勒德”(徽标),曾陪伴成吉思汗南征北战,每一次出征前,大汗都要为苏勒德举行祭祀仪式,作战时将擦拭一新的苏勒德插在战车前。作为重要遗物,苏勒德与成吉思汗的其他圣物一同供奉在成吉思汗陵园内(下称“成陵”),守护、祭祀苏勒德就是班泽尔的职责。
天气预报说这一天风力6级,阵风至少8级,而当天距此不远的阿拉善盟,则刮起了强级沙尘暴,电视画面上,塑料袋、纸片在天空翻飞,肆虐的风沙搅得天昏地暗,令人触目惊心。
阿拉善盟与鄂尔多斯市同属内蒙古高原,是半荒漠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带,阿拉善盟30%为沙漠所覆盖,是北京风沙的源头,鄂尔多斯的沙化面积也高达近50%。糟糕的环境束缚了这对兄弟的腿脚,以至于在全内蒙古的GDP排名中,这两个地区曾长期徘徊于倒数的地位。
不过,几个世纪前,这片广袤的土地却是另一番景象:“河套夹岸,沃野千里”,“阴山之下,草木茂盛,多禽兽”。那时候,这里水草丰美,丛林密布,动物在草地上撒欢,百鸟于林间鸣唱。成吉思汗出征西夏,行军至此,见绿草萋萋,花鹿出没,心旷神怡,不禁诗兴大发:“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得意之中,马鞭从手中滑落,他拾起马鞭,顺手插在地上,对左右随从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吧。”
随口讲的话,不料却成谶语。第二年,成吉思汗病没于西夏朵儿蔑该城。当运送灵柩的大车缓缓地经过鄂尔多斯时,车轮突陷,任凭多少匹骏马都无法拉动。这时,人们记起他说过的话,于是将他就地安葬了。
这个故事在鄂尔多斯草原广为流传,就连目不识丁的老妪也能讲得绘声绘色,“一代天骄长眠地”——类似的横幅标语出现在车站、街头、旅游景点等任何地方。但也有人说这里埋葬的并非成吉思汗真身,只是其“毡包、身穿的衫子和一只袜子”,真身葬在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水发源地的肯特山,在那里,成吉思汗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有关成吉思汗的葬地,学术界历来纷争不止,然而无论哪种说法,都不难让人想象鄂尔多斯草原昔日的风韵,也都体现了成吉思汗本人最后的遗愿:死后不发丧,“勿令敌知”。当时西夏尚未征服,秘不发丧是出于战略之需。人们剖开一棵大树,中间掏空,放入成吉思汗的遗体,外匝三道金箍,深埋地下,不起坟垅,不竖墓碑,而是以千万匹马将埋葬的地方踏成平地,令千余骑兵日夜巡视,待来年春草既生,“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方移帐散去。后来,蒙古人以同样的方式安葬了蒙古汗国至元朝的历代汗王和皇帝,这也是元朝帝王陵寝迄今无一可考的原由。
其实,考证成吉思汗的葬地不过是探秘心理的驱使,蒙古人对此的态度明朗而又潇洒。他们信奉萨满教,相信世上万物都有神灵,人死后,身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魂灵永存人间。大汗弥留之际,守护在身旁的部将遵照传统习俗,从白骆驼额头上取下一绺绒毛放在他的嘴上,吸收了他最后一口气,留下他的灵魂。这绺绒毛连同成吉思汗画像和部分遗物一起,被安放在白色宫帐内进行供奉,从此,这座白色宫帐成为象征成吉思汗的“奉祀之神”和“全体蒙古的总神祗”。
以后,随着成吉思汗四位夫人相继过世,供奉的神物逐渐增多,白色宫帐也随之增加。元朝时,忽必烈在元大都建太庙祭祀成吉思汗等先祖,将太庙定为八室,同时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北岸)也建立了八座祭祀成吉思汗的宫帐,史称“八白宫”,也叫“八白室”。八座宫帐将成吉思汗及夫人的遗物分别安置,各自独立供奉,成吉思汗陵寝开始初具规模。
一代天骄陨落了,缔造蒙古神话的伟人远去了,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还有他的理想和灵魂。八座白色的毡帐不仅是蒙古人告慰英灵、寄托哀思的所在,也是承载所有蒙古人精神的所在,守护它就是守护一个民族的旗帜和希望。从成吉思汗归天之日起,一支精锐之师便从战功卓著、最最忠诚于大汗的部将及其后代中选拔出来,担负起守护和祭奠“奉祀之神”的崇高使命,这支特殊部队就是后来被称为“达尔扈特”的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班泽尔有着一张古铜色的面孔,一看即知是长期风吹日晒的结果。进入成陵之前,他既放牧也种地,成为祭师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天降大任,是家族的荣耀和责无旁贷的义务。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幼子拖雷从尽心尽力支持建立大蒙古国的名将部落中精选出一千余人,交由父汗的爱将、“四杰”之首的博斡儿出统领,命其守卫、祭祀成吉思汗的灵帐。这支部队享有“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并且世袭罔替,代代相传。
由于连年征战,从窝阔台到忽必烈,成吉思汗祭奠一直是简朴的传统祭祀形式。元朝一统天下,忽必烈钦定“太庙八室四季祭祀制度”,将四时大典纳入国事活动。他规范了祭文、祭词,明确了守护、祭祀职责,并封官许愿,正式以太师、太保、宰相、洪晋等大臣的职位命名管理、负责祭祀的人员,这些职位统称为“亚门特”,是守陵人中的贵族。亚门特有八个,实行世袭制,以家族的形式传承,他们分工不同,有主持祭祀的,有筹备祭祀的,有演奏音乐的,还有唱诵的……各司其职,八大亚门特中最重要的太师一职,封给了博斡儿出的儿子。就是从那时起,这部分专司成吉思汗守陵与祭祀的人有了一个专有名称—达尔扈特,翻译成汉语就是“担负神圣使命者”。
“达尔扈特的出现让守陵变得职业化了。”说起达尔扈特的历史,曾任成陵管理局局长的旺楚格这样诠释道,这位自称“半个达尔扈特人”的前任主管在任职期间,将达尔扈特的原始资料做了条分屡析的梳理,使成吉思汗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此之前尽管有守陵部队,但也可以说所有的鄂尔多斯人都是八白宫的守护者。”
旺楚格说,鄂尔多斯并不是蒙古历史上的诸多氏族部落之一,而是像达尔扈特一样,与成吉思汗渊源甚深。
蒙语中的“鄂尔多”是“宫帐、宫殿”之意,鄂尔多斯就是“许多宫帐”。成吉思汗时代没有固定的都城,只以四大鄂尔多的分布处为指挥中心,每个鄂尔多由上千座营帐组成,共万余精兵把守。“你们要不分昼夜保卫我的帐房,不合眼睛地护卫我的身体。”平时,这些精兵强将不离大汗左右,战时冲锋陷阵在最前面。当肩负神圣使命的达尔扈特从他们中间产生之后,他们依然不离不弃,随八白宫移动,环绕八白宫驻牧,渐渐形成了鄂尔多斯部。明朝时,鄂尔多斯人带着“奉祀之神”陆续进入八白宫的始建地河套地区,就此居住下来,鄂尔多斯—这个充满诗意、听起来眼前立刻浮现出华丽的服饰、曼妙的舞蹈、悠扬的祝酒歌的名字,也随之落户于此。
守陵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在清朝,蒙古各部归顺之后。为使因长期战乱而支离破碎的祭祀重新步入正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个盟的蒙古王公贵族联名倡议重组达尔扈特500户,集中居住在八白宫周围,形成明确的禁地,方圆六十里以内不准砍伐树木,不准破坏草场,500户人家专门从事祭祀、守护事务。这一请求得到清政府的鼎力支持,今天生活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达尔扈特即是这500户人家的血脉,300年来,500户已扩展到1700户,人口近6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