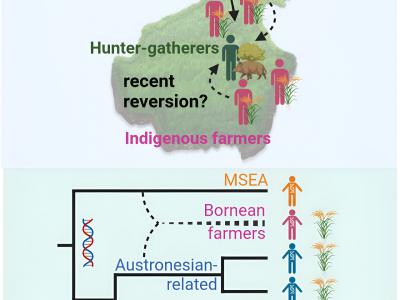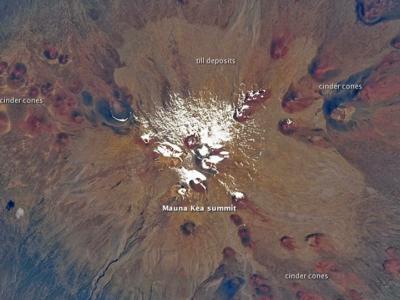马背上的民族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马永远地改变了北美大平原上的生活。有了马,部落能猎捕到过去难以企及的野牛数量;有了马,力量的平衡被打破,马背上的战士取得了优势。马更成为计量财富的标准。对今日美国原住民而言,马仍旧是传统的象征,仍是民族骄傲、民俗仪式与心灵疗愈的泉源。
1874年9月,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北部狭长地带的科曼契骑兵帝国惨烈地走入历史。这个历史事件预示了大平原地区的重大变化,因为自西班牙征服者大军登陆后,科曼契是最早将马引入自己文化的美国原住民部落之一,他们也是其中最成功的部落。他们成为骑术精湛、威风凛凛、气宇轩昂的马上战士,让邻近的印第安部落备感威胁,并以武力攻击遏止白人移民和野牛猎人的入侵,最后甚至成为美国军方的大患。然而1874年9月28日,科曼契最大一支战士部队在帕洛杜罗峡谷毫无防备的临时营地,就在帐棚之间连同家眷被一网打尽。
执行这次攻击的是由罗纳德.史奈德尔.麦肯齐上校领军的第四骑兵队,他们驻扎在德州西部的康秋堡。在突袭了科曼契和其他部族并将他们驱离营地后,麦肯齐的部属烧掉科曼契人的帐棚、摧毁他们的存粮及毛毯,然后在峡谷边缘集合自己的人马以及捕获的一千多匹马。印第安人只能徒步逃窜。麦肯齐带着部队回到32公里外的营地,在次日清晨下令射杀所有马,只留下几百匹备用。 「步兵绑住那些慌乱的马匹拉到行刑队跟前,」S. C.格温在记述科曼契部族的《夏月帝国》一书中记载:「最后留下堆积如山的马尸。」根据记录,共有1048匹马丧命。马尸被留在原地任其腐败,骸骨因为经年累月的曝晒变得惨白。 「这座诡谲的纪念塔昭告着大平原上骑马部落的末日。」大战士酋长夸纳.帕克带领着残余的科曼契人向东走了320公里,来到当时属于印第安领地的西尔堡,宣告投降。
近一个半世纪后,一名研究科曼契族的历史学家托瓦纳.史拜维,坐在他位于俄克拉荷马州邓肯市的宅邸前院,告诉我这起事件的始末。史拜维本身也拥有契卡索人的血统。他指出,屠马事件彻底粉碎了印第安人「反抗力量的支柱」。他们所有的野牛皮袍和食物、他们的生存工具,还有用以交通、作战和游牧的行动能力自此消失殆尽。夸纳也成为阶下囚。 「对科曼契族人来说,这是一次惨痛的溃败。」
以上是发生在帕洛杜罗的著名惨案,但史拜维表示,实际情况比这更糟。 「我们所听到的是大屠杀以及这次屠杀对帕洛杜罗峡谷造成的影响,」史拜维接着补充:我们所没听到的是,到1875年6月,军方又围捕了6000至7000匹科曼契马,回到西尔堡。当时麦肯齐上校已成为当地的指挥官,并遵照菲利浦.谢瑞登将军的指示,以养不起、但放掉又太可惜为由,下令杀了这些马。 「一匹接着一匹地杀马,结果成了个大问题,」史拜维说。杀马既浪费、又笨拙、也很荒唐。最后军方为了节省人力和弹药,开始举办拍卖会,科曼契马于是落入白人买家手里。如果拍卖还不能把马圈里的马清完,杀戮就再度展开。
1874和1875年的这两起屠杀事件虽击溃了科曼契人的反抗,却并未终结流传在美国原住民之间的马的传奇。这只是首批马上战士时代的落幕。其他部族纷纷开始翻上马背。马是新奇的动物和技术,是打猎、战斗和旅行的新工具,它从大平原的南端逐渐向北蔓延,从科曼契族、裘麻诺族、阿帕奇族和纳瓦荷族,传入坡尼族、夏安族、拉科塔族、乌鸦族等等。
马开启了新的可能性,靠着马匹,男人狩猎野牛更有成效,也能走得更远,去对其他部落展开致命突击。靠着马匹,妇女得以免去像是在营地之间搬运家当等繁重的工作。马改变了狩猎部落与农耕部落之间的平衡,让狩猎部族在人口成长、领土扩张上占有优势。马同样取代了北美洲原本唯一的驯养动物,也就是又小又弱,还得喂食肉块的狗。马可以从大地取食,吃的是人类和狗都不要的青草。若遇干旱或冬雪,绿草因此绝迹,它甚至可以靠着白杨树的树皮存活。
这种新动物备受珍视,因而扮演起更抽象的文化角色:可累积的财富。如果一个人精明、有野心,再加上运气,他可以聚积大群马匹。多出的马可卖出、可交换、可送人(以换取更高的声望),但倘若不留心,也可能被偷窃。可累积的财富促进了社会阶级的产生,大平原上首度出现有贫富差异的印第安人。跟随着这件新事物,还出现了另一件新玩意儿:从白人商贩那里取得的枪枝。印第安人时常以海狸皮裘、野牛皮袍或马匹与白人以物易物。这些改变十分重大,带来繁荣,也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商业猎人还没来到之前,野牛其实就已经被过度猎捕了。有了马匹也让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对白人移民和军队的反抗也是如此,最后终于导致悲剧诞生,诸如发生在帕洛杜罗峡谷、蒙大拿州熊掌山(约瑟夫酋长和内兹佩尔塞族人企图逃往加拿大时在此受到攻击)以及南达科塔州伤膝谷的事件。
马带来的革命造成的负面效应已成历史,但对许多美国原住民而言,马的角色仍至关重要,尤其大平原部落更视它为荣耀的代表和传统的象征,并是用来疏导困窘现况的远古价值:马代表了仪式、纪律、勇气、对其他生命的关心,以及世代技艺的承袭。
朋德尔顿集会是个人人都能参加的大型牛仔竞技活动,每年9月在俄勒冈州的朋德尔顿举办,就离乌玛提拉印第安保留区不远。比赛包含了战舞竞赛、几场印第安接力赛,以及在晚上进行的「快乐谷游行」。游行会由大批穿着全套印第安骑士服饰的队伍揭开序幕,浩浩荡荡地在城镇间穿梭。众人在当地酋长的带领下骑马进入竞技场,后方则跟着一群装扮华丽的印第安少女,她们是集会选出来的「印第安公主」。而在后场馬廄旁的拖车上,一名年约50岁的妇人托妮.敏特霍恩是这些印第安少女的指定监护人,她一边缝补仪式专用马鞍的鹿皮软罩,一边向我解释她的任务:「我的职责是把公主们带回马上。」
托妮的母亲曾在1955年当选快乐谷公主,她自己则在1978年当选。在此之前,她成日骑着马、很男性化地长大:她喜欢跟她的哥哥和三个姊妹一起驾着自家的马拉橇、拿着铁杉细枝制成的矛对决,或在马背上嬉闹。她打哪儿学来的骑马技巧? 「生下来就会了,」她说。
托妮继续一面说话一面忙东忙西,又是缝马鞍、又是指导女孩们如何造型打扮、又是透过蓝芽下达各种指示。她童年时住在一个叫作春天谷的小地方,家里没有便利的现代设备或儿童玩具,不过倒是有很多鹿肉及麋鹿肉。小托妮没有洋娃娃。当她班上同学知道了,无比地怜悯她:妳没有洋娃娃? 「我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穷的小孩了。」然后他们又问:那妳平常都做些什么?我们都骑马。你们家有马?对啊。她告诉他们家里有47匹马。 47匹马?你们一定很有钱! 「我就再也不觉得自己穷了。」
另一场重要的集会则是8月中于蒙大拿州克劳亚珍西举办的乌鸦族庆典,吸引了来自南达科塔州派恩岭、爱达荷州哈尔堡以及其他地区的参赛者前往。我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抵达,主办单位十分忙碌,现场更是人山人海。一名中低音的男性广播员欢迎大家莅临乌鸦族联盟今年度的「全印第安牛仔竞技」,以及大会自豪地称之为「世界印第安帐棚中心」的营帐区。庆典节目包括了约1公里的长跑赛、冲刺赛、骑牛大赛、骑鞍马大赛、双人套牛竞赛、女子套犊竞赛,以及最为狂野的印第安赛马接力赛,号称是「印第安国度里最刺激的五分钟」。但这五分钟有时可能只有三分钟――不算抓回脱逃马匹或从地上捡起落马者的时间的话。
印第安赛马接力是团体竞赛,每队阵容里有一名赛马手、三匹马,还有三名英勇的队友要在骑士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时,负责抓住、控制另外两匹马,让赛马手在单趟中轮流骑过三匹马。这些马都没上马鞍。在每一回合里,拥挤的跑道上至少会有五支队伍卖力让赛马手在无鞍的马背间成功跳跃转换、让火力全开的马儿刹车,再骑上下一匹冲刺。这样的场面有可能非常混乱。但不混乱的时候,则极其精采。
身手矫健的赛马手可以瞬间勒马、滑下马身、跑个几步跳上下一匹马,然后抓住缰绳疾驰而去。只要换马顺畅,该队就有机会遥遥领先,不管谁的马速度快。但这才是理想的比赛。我在乌鸦庆典看到的第一场接力赛,有两名赛马手才跳上马背就撞成一团而落马,其中一人起不了身,广播员呼叫救护车带他出场。 「这可是硬功夫,」他说,油滑的语气中没有一丝歉意。 「只有最强悍的印第安人才比得起。如果简单,那唱诗班的男孩也可以上来玩一玩了。」
后来我和索顿.大毛(大家都叫他「提」)聊了起来。这名年轻人身形魁梧,但个性平易近人。他是这届乌鸦庆典中负责竞赛类的委员。他着蓝色衬衫、牛仔草帽,皮带扣还是印第安赛马接力世界冠军的奖牌,那是他在怀俄明州社立丹赢得的。提的体格太壮硕无法担任赛马手,但他略显得意地表示他可是现任「世界冠军勒马手」,都不知道被冲到换马线的马撞倒几次了呢。现下他对当天顺利的赛况感到兴高采烈(我猜也有点松了口气),还向我保证那两名落马的赛马手并无大碍。我从那几天与他和他家人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家族的人天生就爱赛马。
提的父亲丹尼斯.大毛是名71岁的长老,小平头上顶着Resistol牌白色牛仔帽,他身上那圈啤酒肚很难说服人他早年曾是个清瘦的年轻赛马手。我和他一起坐在馬廄区,旁边是他太太经营的肉酱饼摊。丹尼斯告诉我,他14岁的时候就赢了「乌鸦族印第安马赛」,那是最古老的传统乌鸦族竞赛项目之一,差不多在同年还拿下「州长让磅大赛」。当然,他也参加了印第安接力赛。他若有所思地回想,当时他大概才45公斤,不像现在已经110公斤了。他的秘诀是要骑着马紧紧贴近下一匹,然后弹身下马、迈两个大步,从马的后方一跃而上,然后奔驰而去,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切都快得很。如今没人这么做了,他带着点不以为然的感慨。这种赛马方式和部落突袭(暗中盗取其他部落的马),都是已然消逝的优良传统了。
乌鸦庆典也有沉重的一面,庆典会场离小大角战场只有3公里远。小大角古战场「终战丘」下的小丘立着一座纪念碑,悼念战役里丧生的印第安战士。纪念碑上有绘画、殉战者名单,以及碑文,其中包括印第安酋长「坐牛」的怀旧之词:「我小时候,拉科塔族是世界的主宰。太阳从他们的土地升起,也从他们的土地落下。他们可以派出一万名骑士上战场。」
竞技场上的赛事开始后,小大角战场的阴郁历史就宛如过眼云烟。但偶尔仍会出现一些沉重的时刻。在我和提.大毛闲聊的那个下午,一匹纯种马「欧李之子」在冲刺中硬生生跑断了胫骨。眼看只差约20公尺就能称冠了,全场观众一片哀鸣。结果大会不得不在5000人面前枪杀伤马,尸体被拖车移出场外。
翌晨,我再度跟提谈话时,他看起来相当哀恸。 「我心很痛,」他说。他父亲建议他以乌鸦族超然的角度来看待这起事件。但提也告诉我,他对这些马的感情,以及马在他生命里的重要性,在在都让他难以承受。他在胸口握拳:「这是真爱啊!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都该照顾好自己的马。」
印第安赛马接力并非唯一反映美国原住民传统强悍马术的活动。于华盛顿州奥马克市举办的奥马克冲刺赛,紧邻着科尔维印第安保留区,每晚都有一场声名远播(对某些人来说是恶名昭彰)的「自杀赛」作为压轴。人人都可参加这场赛马混战,只要参赛者疯狂到敢骑过一个62度的急降陡坡,直冲进奥卡诺干河里。对马而言,那简直和悬崖没两样。
有些赛马手会在自杀赛开赛前到「发汗屋」中祷告,或以鹰羽装饰马匹。有些则只穿戴安全帽和救生衣,然后自求多福。十几匹马几乎同时下水,游过深水区,奋力登上对岸,然后冲进竞技场,奔向灯光下的终点线。此时赛马手――至少其中马术最高超或运气最好的一些人――已全身湿透,但还要骑在马上。人道协会强烈谴责这项竞赛,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已经有超过20匹马在比赛中死亡。
大会指定的兽医丹.德沃特则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当用不上我的时候,这算是种很精采的比赛。」
隔天下午在印第安营地里,我与编织串珠摊上一名可亲的白发妇女聊了起来,她叫作玛缇尔妲. 「缇莉」.提曼瓦.高尔。在祭典震耳欲聋的鼓声中,她稍微提到了她的家族。他们家都是爱马人,至少可以从她祖父路易.提曼瓦酋长算起。他是育种人也是马商,共养了300匹马。这些马很多都是从附近山上带回来的野马。她还记得在她父亲年轻时,她的路易爷爷派他出门前总是交代:别骑同一匹马回家。 「而他一直都能做到,」她说。她父亲会先套住野马、蒙住马眼、绑紧马脚后装上马鞍。接着再解开马脚上的绳索、跳上马背、拉开眼罩、紧抱着撑过马的狂跳,最后把野马骑回家,他自己的马则一路尾随。
在她的家族中,驭马术绝非男性成员的专利。缇莉的女儿凯西在满18岁那年参加了自杀赛,因为她不再需要父母同意书。那场比赛的结果很糟糕,缇莉描述:凯西从背后被撞,马摔倒了,凯西也跌断一条腿,而他们也不得不杀了那匹马。缇莉从此再也不让女儿参赛了。
这些文化记忆的另一名守护者是玛丽.马强。她是位年届八旬、信念坚定的女长老,膝下有211名子孙,也是科尔维部落同盟的耆老。玛丽和儿子蓝迪.路易斯曾一起悠闲地向我聊起往日时光。如今玛莉已经过世,很多人都对她的离开感到不舍。她那天其实还行动矫捷、充满朝气,身着蓝色缎面衬衫,佩戴镶嵌串珠和鹿角雕饰的项链,头上还有一顶写着
「哈佛」的淡紫色遮阳帽。她记得以前耐力赛包括了8公里的山路,赛马手得骑着马跃过巨石和枝木,俯冲下坡,有时还得涉水渡河。
这种比赛从多久以前开始的?
「这个嘛……」她喃喃地说,一时迷失在时间与记忆里。
于是蓝迪接着回答:「从有马的时候。」
这些或许是部族传统,但对于马的钟爱似乎会如血脉般流传在某些家族里。提.大毛的大家族就是一例。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例子则是黑脚族的年轻女性强娜.拉普蓝。她是来自蒙大拿州布朗宁的赛马手,修长健美的体型足以媲美篮球明星。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朋德尔顿集会里,她一身蓝地骑着纯种骟马参加女子组比赛,比赛里的马不上马鞍,所以通常只有印第安人会参赛。结果她漂亮地赢得胜利。
但接着麻烦出现了。场内一名赛马手落马,骑着马的工作人员高甩套索想追上这匹无人驾驭的狂驹,而这脱序的瞬间让强娜和其他参赛者尽管通过终点线仍无法止速。见一旁工作人员正奋力追逐,强娜的马感到相当困惑,因此也跟着全速奔驰。这时,有名年轻娇小、骑着纯种骝色马的女赛马手不小心让马掉了头,马开始在跑道上逆向疾驰。接下来的惨剧可想而知,站台上几千名观众内心喊着:噢不…… 不……,直到意外发生。那匹骝色马在闪过一匹迎面而来的马之后,一头撞上强娜的骟马。强娜被撞飞,两匹马和那名赛马手也摔倒在地。强娜倒地不起,她的骟马挣扎着起身,但因右前脚使不上力而显得姿态笨拙,那只脚看来断了。强娜最后被大会以担架抬出场。
许多个月后我在蒙大拿州密苏拉遇到强娜,她告诉我那只褐色骟马活下来了。原来它的脚并没有断,只是肌肉受伤,之后就逐渐复原。至于她呢,因为后脑杓被马蹄踩踏造成脑震荡和头皮撕裂伤,流了很多血。但她后来没事了,隔年夏天又开始参赛,再次拿下朋德尔顿集会的女子组冠军。她也在表叔纳西斯.李维斯的接力队上担任控马手。
30岁的纳西斯也是身形高瘦的赛马手,他是强娜赛马生涯中很关键的一个人。强娜在朋德尔顿落马时,人在现场的纳西斯马上赶到她身边。他发现她伤势不重后就放了心,接着便在接力赛中夺得胜利。他是个技巧高超的接力选手,他的身高让他能够像老丹尼斯.大毛一样,直接从马后上马。他跟强娜在同个屋檐下长大,虽是表亲但更像是亲大哥。强娜的马术都是他教的。 「纳西斯总在我身旁,」她说,「若不是因为他,我对马根本一无所知。」
我到布朗宁拜访纳西斯,那是个接壤冰川国家公园东境的印第安保留区小镇。他谈到祖父洛伊. 「卷毛」.李维斯,他是个职业牛仔,当纳西斯还是个小鬼头时,他祖父就任由他在馬廄里打转。 「卷毛」洛伊年轻时常参加牛仔竞技,特别擅长套索比赛。 「从小我身边就都是些适合骑来比套索的马儿,」纳西斯说:「它们不仅速度快,也很伶俐听话。」在那里还有他叔叔史提夫和提姆会指导他如何骑马,他们也都是优秀的骑士。史提夫后来在电影《与狼共舞》中负责马术特技,提姆则到欧洲迪士尼乐园里的「荒野西部秀」表演了九年。
我见到「卷毛」洛伊的那天,79岁的他气势威严、体格壮硕,戴着黑色牛仔帽,披着黑外套,脸上有着深刻的岁月痕迹,双眼闪耀着智慧和风趣的光芒。他讲起李维斯家族的历史。首先,他们有一半法国血统,一半南方黑脚族血统。第二,是马。 「到处都有马,」他谈起自己的童年。马会在馬廄里,会在野外奔驰,若登上坡顶四处望去,也全都是马。 「卷毛」洛伊的爷爷拥马众多,他父亲与叔叔便供给野马给当地的牛仔竞技赛——很单纯的活动:星期天到会场去,试试骑上这些野马。 「在保留区,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的,」他说。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家人、马。我想起了托妮.敏特霍恩在朋德尔顿说的那个没有洋娃娃但有47匹马的可怜小女孩的故事。它为「卷毛」的曾孙女强娜告诉我的话提供了脉络、也加进了时间的元素。强娜的马术是纳西斯教的,纳西斯是提姆叔叔和史提夫叔叔教的,应该也有人教过「卷毛」骑马,或至少让他得以自己领会,所以现在强娜能够教导她年幼的表弟妹。在这名曾赢得两次朋德尔顿竞赛、已成族里女英豪的高䠷表姊指导下,保留区里六到八岁的女孩,或是更大一些的男孩开始在马背上自信昂扬,大放异彩。这种代代承袭的传统也许无法恒久流传,但至少弥足珍贵。
拥抱祖传的技艺和热情;向长辈学习技巧,培养出对马匹的热情;在马术上精益求精,对后辈倾囊相授;用智慧和爱心照顾好自己的动物;把传统交棒给年轻一代;让家族荣耀,而且完整。这就是印第安接力赛的极致。
撰文:大卫・奎曼 David Quammen
摄影:艾瑞卡・劳森 Erika Larsen